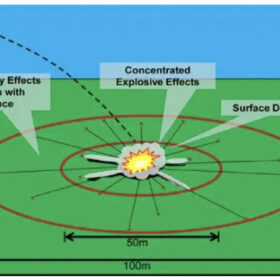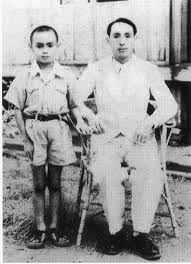田秋堇,〈愛與死 給我的小朋友奐均〉
(1982年2月追思文)
愛與死 給我的小朋友奐均
田秋堇
我以爲黑夜會一直延續下去,再也沒有黎明了。不過黎明雖然是來了,卻是一個很陌生的黎明,從此,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了。

2月28日
車子發動了,軍法處的守衛跑去打開鐵門,我們終於要離開軍法處了。我坐在林律師後面,他的頭在黑暗中顯得大而孤單。張政雄律師一面開車,一面以他一貫不疾不徐的口吻,說著早上開「高雄事件」調查庭的事,林律師聽著,不斷抽煙,應和著他的話。我坐在黑暗中,擔心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到景美軍法處辦交保之前,我向林太太拿輔佐人印章,她從病床上撐起身子,強自鎮靜地說,「林義雄⋯⋯要我把孩子⋯⋯照顧好」(那時她還不知道雙胞胎慘死的事),我已經心力交瘁,只能趕快摟住她說,「林律師不會怪你的⋯⋯」可是一走出病房,自己就哭起來了,我知道林太太擔心的是什麼,林律師就要回來了,可是我們怎麼面對他呢?祖母死了,亭均、亮均死了,奐均身受重傷正在搶救中,我們怎麽向林律師交代呢?
在軍法處,張律師、江鵬堅律師好不容易才和軍法處、保安處的人員談妥,到了10點多,一行人來到會客室等林義雄。起先大家都站著,緊張得很,後來又坐下來,不知道做什麼才好,等了又等,一有人進來,就嚇一大跳,立刻「調整」出久別重逢欣喜的表情。但是,林律師,這些都過去了,你已經回來了,我們要怎麼辦?
到了長庚醫院,有的朋友說先讓林律師洗個澡。我只希望能晚一點讓他知道,先讓他恢復精神再說。但是老康說,今天不講不行,先講奐均和媽媽的部分,亭均、亮均暫時不要告訴他。說完就走進1103病房了。
那時林律師已經洗完澡,正坐在床上,張德銘爲了放鬆他的情緒,把煙斗借給他抽。老康和林律師閒聊了一會,氣氛還算有說有笑。不久就單刀直入地(至少我覺得)告訴他,媽媽的事,再講奐均的事。林律師剛開始還眨動眼睛,表示在聽,後來就只是握著煙斗,一動也不動了。老康說,奐均傷勢不重,醫生正全力搶救,已無危險,林太太正陪著她(事實上奐均還有三個危險期要過)。老康儘量沉穩地說著,一屋子人靜悄悄的。
老康再回頭講媽媽的事,說到身上13道刀傷,林律師只問了一句:「是不是自殺?」老康說不是,林律師一動也不動,我們也擔心得一動也不動,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老康又繼續說了一些激勵和安慰他的話,我覺得那些話聽起來多麼遙遠、空洞,可是如果要活下去,又不無道理。但是林律師只是緊握著煙斗,坐得直直的,一動也不動。最後老康站起來拍拍他說,「義雄,如果要哭,就哭出來吧⋯⋯」林律師突然「哇⋯⋯」一聲,抱住老康哭起來,大家都站在那裏⋯⋯。
他的哭聲這麼慘厲,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男人,這麼慘痛、淒厲、碎裂的哭聲。林律師一直喊:「媽媽!」「我要去看我的媽媽!」不斷掙扎著想下床,老康怕他去看了更受不了,只好說再休息一會,等明天我們都會陪你去。
他的痛苦這麼巨大,把我們沖得好遠好遠,使我們覺得離他好遠,一點忙也幫不上,既不能保護他的家人,又不能分擔他的痛苦,使我覺得痛苦極了。林律師不斷地喊:「媽媽!媽媽!」哭得像個嬰兒一樣,他的頭不斷往後仰,撞著牆壁。最後終於有人伸手去爲他把枕頭扶高,江律師也開始去擰毛巾。
老康又繼續安慰他,叫他要能自制,要能承擔。黃煌雄也安慰他,好像說他現在承擔了臺灣最大多數人的苦難,他的決定也會影響到臺灣最大多數人的命運。可是,林律師,言詞能給你什麼安慰呢?你的痛苦如此龐大、尖銳、痛心疾首。更難過的是,我覺得你很自責,覺得這一切都因為你曾做過的從政決定,看到你那麼痛苦,我們反而哭不出來了。
不久,秀靜(林律師二妹)送衣服來,我出去看到她軟弱無力地靠牆站著,她的臉是我形容不出來的——那是一張悲衰、疲倦得透支,但堅忍的一張臉。林律師一看到她,喊了一聲:「秀靜!」就抱著她哭起來了。她抬著頭,一字一句地哭著說,「這樣也好,反正伊活得這麼痛苦,自從你走了以後,伊活著比死還難過⋯⋯。」
漸漸平靜下來後,秀靜就慢慢對他說,母親過世前,對他已經有了解了。他被拘禁後,有人曾經問她說,「你兒子為什麼要到高雄爲余登發遊行嘛!」她回答,「阮明知道是冤枉的,怎麼能夠不去幫忙?」秀靜又告訴他,媽媽已經會安慰嫂嫂,要她看開這些生離死別了,林律師專注的聽著,臉上傷痛的表情微微熨貼了些。
最後,已經半夜兩點了,大家都走了,我和幾個朋友留下來陪林律師。我們看他了無睡意,為儘量不要讓他想家裡的事,不斷把話題東跳西跳的,引開他的注意,終於天亮了。從百葉窗慢慢透進光線,那些光線,覺得分外驚奇與陌生。過度的悲傷、恐懼和緊張,已使我心神凝聚得解不開了,我以為黑夜會一直永遠延續下去,再也沒有黎明了。
不過,黎明雖然是來了,卻是一個很陌生的黎明,從此,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了。
2月29日
醒來後,忽然聽到一聲:「報紙!」醫院的送報生丢進來一份報紙,我連忙跳起來搶著拿出去。因為林律師還不知道亭均、亮均的事,還不能讓他看到報紙。進門後,林律師說:「秋堇,我要看報。」我緊張過度,竟然說:「沒有報紙。」林律師說,「剛才不是報紙嗎?」我只好搪塞說,警總的人說他不能看報紙,他茫然而「哀怨」地看了我一眼,就沒有再講話了。
早上偷空趕到仁愛醫院探問奐均的病情,再回到長庚醫院後,推開1103房門,只見一屋子呆滯的臉孔,空氣凝結。我趕快退出來,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說,「已經告訴他雙胞胎的事了。」天啊!我趕快再進去,還是那些凝結的臉孔。
正不知道怎麼辦時,人群中一陣騷動,麗貞(林津師么妹)跌跌撞撞哭著進來了——我從來沒看見她那樣,她的臉因剛生產而顯得浮腫,過去我看到她時,她都是明麗、活潑的,但是現在她蹲在哥哥膝前,只是仰著臉,淚流滿面,直直的看著哥哥,她不斷抽泣,但還是死死地瞪著哥哥的臉,而我已經不忍心去看林律師的臉。麗貞的臉,在晨曦中格外清楚,我蹲下來,她的臉離我很近,給我一種放大了的感覺。我覺得那種恐怖的痛苦,似乎給她一種超乎平常的力量,但她的力氣也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限了。
林律師已經沒有力量哭了,他只是木木地流著淚,沙啞的對麗貞說:「麗貞啊!做和尚也比這個好啊!」
不久,朋友把我叫到一邊去,說老康叫我不要哭成一團,要我叫大家出去,讓林律師安寧,他要到仁愛醫院去接林太太來(讓林律師告訴林太太雙胞胎的事)。我哪有力氣「請」大家出去,講了一兩次沒有人聽到,就沒力氣,還是老康來「喊」大家出去。
我們和老康來到仁愛醫院,由一個朋友陪林太太從防火梯離開醫院,我們留在病房門口「吸引」記者的注意。等我回到長庚醫院,病房外面已經人聲鼎沸,人山人海了,據說林太太聽到雙胞胎的事,昏了過去,護士趕快給她打針。1103病房現在「門禁森嚴」,除了護士誰也不准進去了。
下午來到長庚醫院,進到病房,林太太正坐在椅子上,我摟著她,她說,「你們為什麼要騙我?」我說,「我們不是要騙你,昨天我們都為你擔心得要死。連我們自己都受不了,我們怎麼敢告訴你?而且那時奐均的手術情況還不明⋯⋯」正說著,有人拍拍我,要到殯儀館去了。
趕到殯儀館,只聽到林律師喊媽媽的聲音,和洋子(林義雄大妹)的哭聲,裡面不斷傳來林律師用頭猛撞冰櫃的碰撞聲。有人喊:「醫生!醫生在哪裡?」大家不斷找醫生,麗貞已經呈半休克狀態了,醫生及時趕來替她打了一針強心劑和鎮靜劑。
林律師和林太太終於被扶出來了,宜蘭的鄉親在後面攙扶著林律師。我和一群不認識的人拿著香,被守衛劃爲第一批,進了停屍間,我一直以爲我很堅強,可是一看到祖母躺在那裡,蓋著白布,就哭起來了,喊了一聲,「歐巴桑」!就走不動了,我還是不相信她們已經死了。我哭得一步也踏不出去,守衛很不耐煩地過來催我,說我阻礙了隊伍。我淚眼朦朧中,抬頭看到兩個小小的頭並排在一起,喊了一聲,「亭均!亮均!」覺得一切都完了,這是真的了?亭均、亮均,這就是你們?天啊!你們一定還活著——
和刑警隊約好做筆錄的時間已經到了,朋友「架」著哭泣的我,把我帶到信義路。可是一下車,遠遠望見那扇熟悉的鐵門,牆頭的花草和半圓型的波浪塑膠板,所有的回憶霎時都湧上來了。等一下她們就會來開門,她們還在,祖母憂傷憔悴但安靜的眼神,還是瞧著滿屋子亂跑的孫女⋯⋯可是只要一走進去,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漸漸想到,我要趕快做筆錄,趕快把壞人抓到,爲亭均、亮均報仇⋯⋯。我勉強走到主臥室,坐在椅子上,一個高大個子的男人(後來才知道是鄭隊長),就一屁股坐在我對面的床上,剛好坐在奐均那天躺著的地方,我實在想忍住了,不叫他坐別的地方,可是實在受不了,那是奐均躺著受傷的地方,那是恐怖、驚嚇、悲傷的起源,是我永遠無法忘懷的地方,他不能坐在那裡!我實在受不了,只好顫抖著說,請你不要坐在那裡,他只稍微挪動一下。我只好對他講明,為什麼不要他坐在床上。
做完筆錄,走出大門,遠離了信義路的房子,我忍不住又哭了,多麼破滅啊!即使昨天我送奐均去醫院的時候,也不知道這房子裡,包藏著這麼多的死亡和痛苦!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生命裡破滅了,我漸漸遠離的,不只是信義路三段這棟房子的深色鐵門而已。
3月10日
今天林律師說要帶我去看奐均,我高興得拍手叫起來,好想念她,自從把她送到醫院以後,總覺得她的生命和我有某種關連。
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2月29日陪林律師到仁愛醫院看過她以後,就一直沒有再見到她了。那天她鼻子插著綠色管子,虛弱地對爸爸微微一笑的樣子,在我眼前浮起。推開病房的門,我看到奐均坐在那裡,和護士阿姨在玩遊戲,她穿著粉紅色的小睡衣,氣色煥然,頭上盤著兩個小辮子,像個奇蹟似的。
她和林太太玩「公雞、母雞、小雞」的樣子最可愛了,她笑著唸:「我家的我家的,我家ㄑㄧㄝˋ!」猜拳輸了就用手在嘴前比個小雞嘴的模樣,贏了就舉起兩手,合著手掌豎在頭頂做雞冠,不輸不贏就兩手叉腰,做「母雞」。她的反應很快,但做公雞的時候,手總是舉不高,手掌合不太起來,好像那個雞冠有點痛似的,看了很叫人憐。林律師趴在旁邊的病床上,看著她,眼睛漸漸濕了。
我們終於要走了,林律師一直哄她,要她唱「爸爸的煩惱」:爸爸,爸爸,你不要煩惱,爸爸,爸爸⋯⋯。
但是她看到安全人員開始進來,打開安全門,準備要走了,就顯得有點不高興、委屈的模樣。我想,她希望爸爸媽媽留下來,可是又知道不可能。她要我留下來陪她,我又有事不能留下來。她好像有點急,神情似乎很想說,「不要走嘛,你們不要走。」可是她又不說。
我們終於走了,我坐在車子裡,眼淚不斷掉下來。奐均還活著,生命多麼奇妙,她像一個珍貴的見證和禮物,重新帶給經歷浩劫的這家人生命和希望。可是,我越覺得她像個奇蹟,就越感到祖母和妹妹的死亡,那種黑暗的、沉重的絕望。
◻︎ ◻︎ ◻︎ ◻︎
今天做「二七」,晚上10點多,我們出發到信義路去,一路上我擔心林太太,不知道她受不受得了,自從28日她離家到景美軍法處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回家。
黑暗中,窗外的燈火不斷流逝。樓房森然,這一切都像是一個龐大沉默的預言,彷彿這世界知道它的命運,可是不肯告訴我們,使我們不但要承擔過去的痛苦,還要負荷未知的不安。
下車後,林律師、林太太和我魚貫而入。林太太到了玻璃門前,想彎腰脫鞋,可是彎到一半,就哭起來了。7年來,她曾在相同的地方做過多少次相同的動作,可是,等她回來的人,如今在哪裡呢?
我扶著她,她哭著跪下去,秀靜爲她披上長蔴帽。林太太顫巍巍地站起來,哭著說:「亮均、亭均,媽媽回來看你們了⋯⋯」她們兩人,從相框中向外微笑著,看著媽媽。亮均手叉腰,亭均在她後面,兩手搭在她肩上做「火車」,那模樣頑皮可愛極了,相片又剛好是在客廳拍的,好像她們還在這裡似的。
林律師帶著林太太一間一間地看房間,經過的每個房間,都熟悉得令我顫抖:祖母的臥房、廚房、奐均的臥房、浴室、小熊⋯⋯,一切都像一場惡夢,每一樣東西都使我覺得:「她們還在!」我一直想衝到地下室去救她們,她們很害怕,可是沒有人去救她們⋯⋯,亭均、亮均!
林律師要我到靈桌上去拿亭均、亮均的相片,我緊緊地緊緊地抱著相片,好像她們小小的靈魂就在那裡面似的。原來,林律師要把相片放在鋼琴架上,彈琴唱「我的邦妮」給亭均、亮均聽。
回到醫院已經快一點了,在醫院裡,林律師還是走來走去地唱著「我的邦妮」,不知是他的歌聲本來就不好,還是悲傷過度,聲音破碎沙啞,再加上曲子有點走調,聽起來分外悽涼。聽著他一直沙啞、有點走調地唱著那首歌,我都不禁有點擔心起來了。
◻︎ ◻︎ ◻︎ ◻︎
今天做「滿七」,下午5點和林律師、林太太一起到信義路家裡。我看秀靜很疲倦的樣子,問她爲什麼,她說,從4點多就開始誦經,大部份的時間她都跪在靈前,又要煮飯,心情又沉重,我看她憔悴得好像快要垮掉了,不禁覺得有時候,要活下去好像需要更多的勇氣。
到了晚上11點多,法師說時間到了,林律師、林太太、洋子、秀靜、麗貞,開始在門外燒紙錢和衣物給亡魂。林太大拿了亮均、亭均的一些用品,其中有個小小的書包,林律師捨不得燒掉,要她放在一邊保存起來。
我看著熊熊的火舌在成堆的紙錢上,不斷跳躍,好像有生命一樣。它們不斷地吞噬著東西,把這個世界的訊息帶給她們:錢、外套、亭均亮均的小睡衣⋯⋯。
他們5個人手拉著手,圍成一圈,林律師和林太太各以一手抵著家宅的圍牆。看他們圈著火堆,給我們一個奇異的感覺,覺得她們所環繞的,是一個靈異的世界。她們的影子給火光烘照得詭異、高大,映在四周的樓房上,火光在一片黑暗中,直上天聽。秀靜、麗貞她們都在哭,火越來越旺了,火苗越竄越高,彷彿那堆火是母親,是亭均、亮均⋯⋯。
火慢慢「收走」了那些東西,漸漸縮小熄滅了。但是我一直記得他們的臉被火光照得通紅的情景,他們手牽著手,站在寂靜夜深無人的街道上,哭泣著注視火焰將他們的愛,帶給最依戀的母親和亭均、亮均⋯⋯。
(原載於1982年2月《八十年代》)
輯自《落花春泥與新芽:林游阿妹女士百年誕辰 林亮均林亭均受難四十週年紀念文集》(宜蘭縣五結鄉:財團法人慈林教育基金會,2022年),頁50-57。
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惠允「台灣放送」轉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