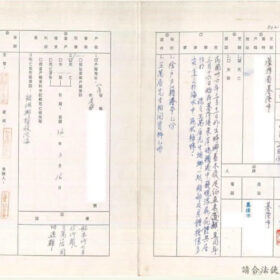海洋之子鄭成功(八)
周婉窈
永曆十五年(1661) 四月一日 ,善打海戰的鄭成功率大軍入鹿耳門,初四普羅岷西亞城(赤崁城)投降,但之後足足花了他八個多月(永曆15/04/04-12/13),困守熱蘭遮城的荷蘭人方才投降。我們今天對於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可不是「收復」臺灣;非己之物何來「復」?)通常抱持著正面的看法。何以如此是有長久的歷史背景,在此無法深論。讓我們設法回到歷史的現場。當鄭成功決定攻打臺灣時,眾人不敢違逆,但頗有難色。即使大軍在金門料羅灣等候風勢,要遠渡重洋攻打臺灣的那一刻,都有不少士兵逃亡,還得特派專人負責搜捕捉拿。熱蘭遮城長官揆一投降之後,鄭成功嚴令搬眷,鄭泰、洪旭、黃廷等將領公然拒命。顯然鄭成功往平臺灣,以安頓將領官兵家眷的美意,不是所有將領都能心領。誰放心把家眷安置在一個遠離大陸、波濤難渡的陌生島嶼?
從歷史的大場景來看,鄭成功攻取臺灣,大失反清復明志士之心。他的老師錢謙益雖然降清,但在師母柳如是的影響下,暗中支援復明運動,還差點喪命。陳寅恪先生感嘆到:「嗚呼!建州入關,明之忠臣烈士,殺身殉國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懸海外之雲(指延平王),目斷月中之樹(指永曆帝),預聞復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就是箇中翹楚。她和錢謙益把大明九鼎的希望寄託在這個來自福建的學生。但是,當鄭成功攻取臺灣的消息傳來,錢謙益認為鄭成功既然以臺灣為根據地,則更無恢復中原的希望,所以那一年快到除夕時,他從白茆港的別墅芙蓉莊移居城內舊宅,柳如是則仍然留在芙蓉莊,直到錢謙益將死之前才入城。何以如此?陳寅恪先生說:「殆以為明室復興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猶有可能。……」陳寅恪先生認為錢謙益和河東君在白茆港居住,主要就是為了和「海上」通消息;海上指鄭成功,是歷史現場的語碼。在亂世,女子如柳如是者,往往比男子更執著,更能堅持到底。是這樣吧?

在「有悵寒潮、無情殘照」中,我們的美人柳如是佇立江邊,雙頰泛紅,袖口猶帶芙蓉莊初綻放的梅花香。寒風中短小俐落的身影,讓人覺得「總一種倔強,十分憔悴」。海中之雲那麼渺不可尋,而月中之桂,突然斷折……
這是個如果不甘心降清,是越來越孤單、寂寞,並且必須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時代。您可以想像嗎?您所認識、所尊敬、所摯愛的人一個個以不同方式「死之」,而您卻還活著。要靠怎樣的力量才能繼續活著?繼續活在死亡的蔭谷。光是活著已經很不容易了,何況繼續抵抗。從吳三桂為「我那人」引清兵入關,到鄭成功和荷蘭人簽訂和平條約(永曆15/12/13;1662/02/01),已經十七年又九個月了。若是嬰兒呱呱落地,此刻已經長大成人。
張煌言的妻子董氏和兒子萬祺已遭禁錮九年。只要他降清,不惟妻子平安,且馬上寵遇有加。但是張煌言一開始即覺悟到國破無法保家,不為所動,但他不關心妻子和唯一的愛兒嗎?當然不是,他感念「妻子顛連,無以存活,故終其身不蓄一姬侍」。終是有情人,雖然他在〈擬答內人獄中有寄(己亥)〉一詩中寫到「名教自束躬,柔情非所躭」。張煌言擁戴魯王監國,和鄭成功屬於不同抗清勢力。唐王、魯王之間有嫌隙,閩、浙勢如水火。張煌言為了釋兩國之嫌,曾自請出使閩地。唐王崩殂後,鄭成功崛起,英雄惺惺相惜。張煌言曾說:「招討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聽了,也說:「侍郎始終為魯,亦豈與吾異趨哉!」(難道和我有不同嗎)兩人遙奉永曆帝,而始終各為其主,相互敬重,並曾於己亥年(1659)一起會師北征,震驚天下。
說到這次北征,最令張煌言一生扼腕。這是鄭成功第四次北征,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史稱南京之役。鄭成功的軍隊原有左、右、中、前、後五提督,北征動員四提督從征,只留前提督黃廷留守金廈。此次北征與鄭成功過去的征戰風格不同,朱希祖指出:「鄭成功專顧根本之地,不肯長離閩海。」鄭軍聲勢浩大,氣如長虹,揚帆直入長江,勢如破竹,破瓜州、克鎮江,近逼南京城,眼看歷史就要改寫了……,如果鄭成功聽從建議的話。由於大船艦逆流速度慢且笨拙,張煌言建議應該從陸路而非水道攻南京城,但未被採納,以至於南京城有時間備戰。在作戰策略上,由張煌言率水師側擊觀音門,以呼應鄭成功攻打南京城,但當他抵達時,鄭軍遲遲未到,導致張煌言孤軍作戰,損失慘重。如果當時能即時夾擊,南京城很可能一攻而下。之後張煌言硬是被鄭成功派往蕪湖,從此無法參與戰略的籌畫。看來是有意支開他。
鄭成功最大的錯誤是,以為南京城只要圍困一久,必能下,因此未作他圖。這同時,被派往蕪湖的張煌言則收穫豐碩,長江南北相率來歸附,或招降,或克復,共獲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此時鄭成功圍南京城已經半個月,未發一箭射城中,而且鎮守鎮江的將帥也沒出兵攻取鄰近的縣城,張煌言得知後,深知不妙,即寫信給鄭成功,大意是說:讓軍隊只是消極地圍著堅守的城池,「師老易生他變」,也就是軍心鬆懈,容易出意外;最應該分遣諸帥,盡快攻占南京城附近各府,如果南京出兵來援助,我方可以夾擊殲滅他們,不然只是守住敵人而已;等四面都攻下了,即可以全力攻打南京城,那時候,南京城就像牢籠中的羊、地窖中的野獸一樣。然而鄭成功從舟山興師,一路「戰必勝、攻必取」,因此頗自驕,連身邊大將甘輝勸誡他不要中了緩兵之計,都聽不進去,哪還聽張煌言的。可惜,張煌言不幸而言中。

鄭成功的軍隊圍困南京既久,士兵放下武器嬉遊,到處打柴割草,營壘一空。清軍偵知這個情況,派人與外聯絡,裡應外合。一日清晨,鄭軍伙食還沒準備好,南京城門一開,衝出一支輕騎軍隊,擊破鄭軍的前營,鄭成功倉促移帳。由於兵士還沒吃飯,毫無鬥志,大敗。此時來援助的清兵,由後方夾擊,鄭成功軍隊潰敗如山倒。最讓張煌言不可理解的是,他想南京城即使暫時挫敗,未必馬上上船;即使上船,未必馬上揚帆;即使揚帆,也一定還會守住鎮江,萬萬沒想到鄭成功不但捨棄南京城,也捨棄鎮江,大軍急急撤走。在震驚和失望中,張煌言決計往西攻打江西,但是此役失敗,開始山間逃亡歷程,從率有軍隊,到只一僮一將相隨,間關百折,方回到浙江海濱。總共徒步走了二千餘里。這段歷程,驚險萬分,若非靠輾轉仰慕他的陌生人幫忙,萬無生理。回思南京之役,張煌言感歎說:「乘勝長趨,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勞瘁殊形,是又戲耶、夢耶?」直是「痛定悲疇昔……至今頻扼腕」。
何以鄭成功撤退得如此倉皇?或許他習慣顧根本之地,很少長離閩海,南京城外大敗,突然間感到非盡快回到金廈不可。鄭軍撤退得很狼狽,犧牲慘重,也損失好幾名重要將領,包括甘輝──死得很慘烈。
(未完待續)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09/01/02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