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特輯 訣別的悲劇
高彩雲口述、高永清紀錄(日文)
潘美信譯、周婉窈校訂
說明:這篇高彩雲口述記錄,是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在去年「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中提供給本平臺的。 高先生是高彩雲的弟弟Awi Tado的長子。高彩雲,族名Obing Tado,日本名高山初子,是花岡二郎的妻子。譯者潘美信女士是高彩雲的媳婦,也就是花岡二郎遺腹子高光華(Awi Dakis、中山初男)的妻子。很可惜的是,口述日文原稿經人借走後未還回,導致我們無法比對原文。
Obing Tado(高山初子、高彩雲)也就是電影《賽德克‧巴萊》中徐若瑄飾演的角色。該電影預告片有這樣的片段:初子避難時,日本婦人排斥她說:「你不也是番人嗎?幹嘛也跟我們一起躲?」接下來初子從屋縫拉住父親的披巾,哀哭說:「とうさん(多桑),為什麼要出草…」這篇口述資料顯示以上的情節不符合她所回憶的景況。當然我們無法責電影以史實,只能希望落差不要太大,即使貌離也能神合。我個人非常期待這部電影能有大突破;當代人以在地的歷史為素材,發揮想像力、創造力,將我們的文化和藝術提升到另一層次,是很艱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需要社會大眾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個人常覺得真實的世界,如果我們能探觸到那「真實的底面」,往往比虛構還能撼動人心,私意以為藝術無非是要探觸到那個底面。我們該期待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應是在這個層面吧。
這份口述記錄不長,但提供了若干重要訊息,例如:在宿舍牆壁寫遺書的是一郎(另一說是二郎),而且穿著正式的族服(為安全起見,或代表心境和立足點的改變?)。莫那魯道很擔心Tado Nokan的大女兒(初子)被誤殺,一直尋找她。這段記載,如果屬實未加演義的話,好像讓我們稍微能夠接近英雄的心。初子避難時,心境經過幾番轉折,也很值得留意──她一開始將追殺他們的原住民當成「敵人」,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族人和馬赫坡社赫然是「起義的元兇」!一郎、二郎下山探情況,回來後的沈默,以及「必死」的決定,給人沈重之感。族人集體自縊的過程,讀來令人動容。當然,高彩雲的回憶也反映了戰後多方面的影響,這點想必讀者當能分辨。
為求存真,本刊除改正明顯錯字外,盡量不更動中文原譯文。補字記號〔〕、按語,以及注釋係本人所加。(周婉窈2011/08/18)

我與花岡二郎是昭和四年(1929)10月27日,和花岡一郎和川野花子同日舉行婚禮。當時一郎是霧社派出所的乙種警察,二郎是警手(服務員;按,類似警察助理)。我們兩位當時是埔里小學校(日本子弟就讀的學校),是高等科二年級。[1]當時日本政府的命令,由高等科二年級退學返鄉舉行結婚,這門婚事很可能日本政府早已有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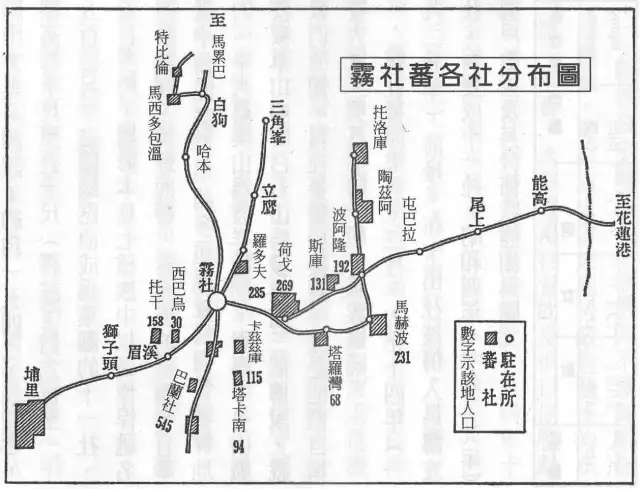
婚後花岡一郎派至馬赫坡(マヘボ,今蘆山溫泉)蕃童教育所任教,過了不久調到坡阿崙(ボアルン)教育所(今蘆山國小)任教。[2]昭和五年(1930)10月25日一郎夫婦抱著剛滿月的兒子幸男到霧社家[3]住宿,10月26日晚上有聯合晚會。第二天早上舉行一年一度的聯合運動會,因此一郎及二郎為著此次的盛會忙得不可開交。
27日一郎及二郎起得特別早,即刻到武德殿,現在來說是比藝之場所。他們花了約一小時在那兒勤練劍道術(是當天他們兩人必須表演的項目──「劍道」),練完劍道之後就帶坡阿崙教育所的學童到運動場。我與花子帶著便當出發到國小(按,霧社公學校)操場,在街上稍停下來到店家買糖果,也花了一些時間了。
當我們抵達學校運動場時,同時看到在〔有如〕阿修羅的巷子(目前高德造長老住的地帶)有槍聲……慌恐的走避,尖叫聲…一片慌亂,每個人無目的地竄逃。
至於我及花子毫無目地要往何處走?我們兩個人驚慌地各自逃走。我就與小學生一起往新原〔重志〕校長的宿舍飛跑過去而躲在那兒。
原住民同胞追擊至新原校長家廚房時發現堆積許多日本人的屍體,[4]我被屍體堆在下面快沒辦法翻身,在那時志柿〔源次郎〕公醫夫婦被原住民同胞追到校長家的廚房逃難,而原住民同胞從牆壁的裂縫將槍口深入瞄準志柿公醫,一槍斃命。他的夫人大聲哭號著:先生您怎麼可以丟下我而一走了之呢?我馬上向她禁止絕對不可大聲哭號!!敵人埋伏於外面,如此我們兩個都必被〔槍〕彈收回生命。

因此兩人假死不敢出聲,埋伏於外面的戰士們認為已經沒有活命的人了,安心退回去時,忽然從外面聽到莫那魯道的叫聲:Tado Nokan(達多諾幹)的大女兒是不是被誤殺了?一直耿耿於懷地尋找我,接下來我的姑母(父親的姐姐)名叫Obing Nokan,以高昂的叫聲呼喊我,〔我〕清楚地聽到,但不敢發出聲音,我才知道馬赫坡(マヘボ,今蘆山溫泉)和荷歌(ホーゴ,今春陽部落)同胞是這次起義的元兇。
我從屍首之間掙扎而出來,要向外面走出時,志柿夫人制止我不可到外面。但我告訴夫人,妳就持續安靜地假死於原地方,看了好的機會就有人來救妳,請勿離開。與 公醫 夫人講完話之後,〔我〕就往外走出去時,看到姑母(Obing Nokan)我即刻向外跑上抱住她
運動場至分局這段路遍地都是屍體。
大約上午十點回到宿舍時,一郎在此宿舍牆壁寫一遺書,他是穿著正式原住民服裝。
27日晚上回ホーゴ(荷歌[5])的家但不敢在那兒住宿,而到小山崗小睡,28日早上男士全部武裝準備應戰,因為我們已經下定決心要對抗日本人高壓政策的心非常堅定,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們一大家族往森林方面避難,那時我的家族,二郎家族,一郎夫婦的家族,總計二十多人。
28日晚上計畫全體人員決定要死,每個人手中都準備麻繩,每個人選擇適合的枝榦要結束生命。在成仁之前川野花子之母是父親的姊姊Iwan Nokan。她自己編歌詞而唱:「媽媽,我們二十多位親戚,現在就要到媽媽的地方見面了,我們二天都沒吃飯,現在肚子非常飢餓,請帶著便當到途中迎接我們喔。」剛唱完訣別歌之後,從山腳下有男人大聲叫喊著:「等一下!」向山上趕著上來了,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山上衝上來──原來是一郎和二郎二人。他們說:「要上吊的時機未到,請下山。」因此準備要成仁的計畫暫時拋開,都將繩子解開,從樹上下來。那天晚上一群人在大樹下露宿,過了一個安靜夜晚。
29日早上一郎及二郎將我們留在山上,他們下山去了。到下午四點回山上來。他們兩個人雖沒說半句話,但是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以死表白自己的決心。
同時從濁水溪方面有パーラン社(霧社;按,巴蘭社)川野花子(一郎太太)之姐姐及姐夫(Walis Tiwas)突然來到眼前,要接我們去パーラン社(巴蘭社)他們姐夫家避難,我的母親、姑母(Obing Nokan)都同意帶我的弟妹去依靠親長,但是一郎夫婦及其他親戚是決心要成仁。夫二郎也是堅決要成仁──我是非死不可的。
他說:「妳是女人,日本政府不會對女人定罪的。妳要好好勇敢地活下去,一切就由命運去決定,要好好保重身體及肚子的胎兒。我們要先走了。」說了上面一段話之後,我們沿濁水溪旁走往霧社,他們又回到森林中。
我與母親及姑媽和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共八人,被安排到バーラン社(巴蘭社)アウィテワス(Awi Tiwas)家時,為10月30日下午二點左右,部落冷清,只有狗的叫聲,非常冷清。日人安排族人不時巡視四周圍有否可疑人走動,當時パーラン社(巴蘭社)分局官員是石川源六,村內頭目是Walis Buni[6]。我總是憶起夫二郎及一郎夫婦及剛滿月的幸男,以及二十多位的族人決心自殺的情形,幕幕在眼前。
我和夫二郎道別下山之際,一郎抱起剛滿月可愛的兒子幸男,一面說話,一面流著淚。我看了也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淚……。一郎抱著可愛的嬰兒說:「孩子阿!請原諒爸爸,我們是不適合在這世界存活的命運,爸爸的手要將你也跟我們一起成仁,我們將向神祈求要息世上的痛苦,到天國去了。」
二郎站在一郎旁,聽到了那一番話突然啞口無語。此刻想起初子的腹內孕育了我們的骨肉,於是一郎特別向我說:「你不可以輕易地向死神低頭,要克服一切的難關及困苦,為著腹內的小生命必須勇敢地活下去。」當時一郎對我說的這番話,至今仍在腦海中停留著,想要忘記始終都忘不了地刻骨銘心。
我逃到パーラン(霧社)第三天,石川源六部長要召見,事件之後石川部長一直逼問一郎及二郎的下落。我的心非常疼痛,無語問蒼天,只好說「不知道」。如果說出真相,後果不堪設想……等待命運的安排吧!同年11月8日田村憲治部長傳喚我,告知一郎等二十多名集體吊死的屍體已發現,得知惡耗之時,生離死別的日子已到了,我向天跪地哭號著,已潰堤了。同年11月9日田村部長(霧社事件前)在ホーゴ社(荷歌社,今春陽)勤務,而事件前半年調往埔里分局,因此田村部長對於ホーゴ社的地理環境很熟悉,就陪我到一郎、二郎及族人的二十多名成仁現場,由警察帶幾名軍伕用石油在現場火化。
我就想起10月28日一郎、二郎及親族二十多名要成仁未遂的地點,有大棵樹木四方八達,其樹枝可容二十多名。族人穿著傳統衣服,看到遺容是那麼熟悉,而今卻天人之別,哀哉!
二十多位族人選擇自己中意的樹枝套上繩子要結束人生之路,在大樹的正對面有一郎夫婦及初生嬰兒幸男,面向上用新的毛巾[7]蓋上臉,一郎夫婦及二郎穿著去年結婚時的日式禮服。打開和服仔細觀察,始知一郎以番刀自殺腹部,大腸流出,妻子(花子)及幸男用番刀砍了頸右動脈切斷。確定是一郎自己下手了斷妻、子的生命。一郎將刀子沒有放入鞘內。縊死的人都用新毛巾蓋上臉,唯有二郎一人沒蓋上臉部。由此可想二郎是處理所有的縊死或用刀刺死的人們之後,並且為我及肚子內的親骨肉以及族人的靈魂要上極樂天國之事,完全交代好之後,找了較低的樹幹結束生命了。
唯有他(二郎)的臉部未蓋上毛巾,由此可推斷是他將二十多位成仁的人們一切的後續整理工作完成後,自己最後用備好的麻繩綁在樹榦上而結束了其一生。並且為了先走的親戚族人的靈魂升上天國而祈求、以及為了我及遺腹子的健康幸福向神祈求保佑,一切順利平安後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田村部長命令自己的屬下將屍體由樹上解下來,並由四周收集枯木來用石油火化所有犧牲的原住民們。我自己也被警方帶上山來認屍後,點香祭拜成仁同胞們、花岡二郎及一郎全家人,讓他們能安息主懷。之後我帶著疲憊而失望、寂寞的心情下山返家已是太陽西下之時,充滿疲憊的身心回到パーラン(霧社)時,〔在〕伯父Watan Nape的家等待的母親及姑母(Obing Nokan),〔我〕將所遇到的情況再次詳細告訴她們。於是她們二人為女婿(二郎)及同族的二十多位成仁的族人哀痛,並且整夜小聲哭泣著……。
往後這座小山,日本人取名為「花岡山」。
成仁之後,日本政府有為二十多名的犧牲者造墓,將骨灰取下埋於那地方。事件之後親日的ホーゴ(春陽村)的村民(按,應該是指都達群)分到花岡山的畑地(按,旱田)。他們在那兒開墾,因而墓地變為他們的耕作地,變為一大片的耕作地。原來的墓園的風貌消失了。


附錄
高彩雲女士口述記錄中的人物關係簡介
周婉窈
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過去曾被誤為親兄弟,其實不是,倒是因為婚姻而成為連襟。花岡一郎族名Dakis Nobing,花岡二郎族名Dakis Nawi,同屬荷歌(Gungu)社──事件中起而反抗日本的六社之一。他們兩人都是統治當局特意培養的原住民青年,日本名字也是當局所取。二郎出身荷歌社頗具勢力的家族,一郎的父親是普通的族人,母親是荷歌社的巫醫。一郎和Obing Nawi結婚,二郎和Obing Tado結婚。很巧的是,二位男子都叫Dakis,二位女性都叫Obing。和一郎結婚的Obing,日文名字是川野花子,也就是電影中羅美玲飾演的角色。兩位Obing其實是姑表姊妹,川野花子是高山初子(高彩雲)的父親Tado Nokan的大姊Iwan Nokan的女兒,若用漢人的概念來說,就是大姑的女兒。
Tado Nokan是荷歌社的頭目,換句話說,一郎娶了頭目大姊的女兒花子,二郎則娶了頭目的女兒初子,一郎、二郎於是變成連襟;在日文來說,就是「義兄弟」了。附帶一提,初子大伯的女兒Obing Lubi嫁給莫那魯道的次子巴索莫那,莫那魯道的二女兒則嫁了初子二伯父的小兒子,可見荷歌社頭目和馬赫坡頭目兩家之間關係非常密切。
荷歌社的頭目Tado Nokan在事件中戰死。這篇口述記錄提及的另外一位初子的姑媽Obing Nokan,是Tado Nokan的二姊(前一任頭目的二妹),和綽號「生番近藤」的日本人近藤勝三郎結婚(後者其實是重婚),後遭遺棄;勝三郎的弟弟儀三郎是巡查,和莫那魯道的妹妹結婚,調到花蓮後失蹤,莫那魯道的妹妹只好返回部落,女方感覺是故意遺棄。換句話說,荷歌社頭目的妹妹和馬赫坡頭目的妹妹和一對日本人兄弟分別結婚,都遭遺棄。
口述紀錄中,在一郎、二郎親族決定自縊時,出現在現場的是川野花子的姊姊和姊夫。花子的姊姊嫁到巴蘭社,該社沒參與起事。若不是他們出現,很可能初子就和家人自殺了。結果是初子和母親、遭日人遺棄的二姑媽Obing ,以及弟妹,共八人,前往巴蘭社避難。一般看到的說法是,只有初子一人離開決定自縊的族人,包括她本人的陳述也大都作此。這份口述紀錄則很不一樣,孰為真?待攷。
筆者在整理這份記錄時,感到有不甚能了解的地方。川野花子的姊姊是初子的表姊,她和丈夫來接親人到巴蘭社避難,最親的親人應該是母親Iwan、妹妹花子、妹婿一郎,以及花子和一郎剛滿月的兒子幸男,但結果三個大人決定帶著嬰兒自盡;勸走的是阿姨、舅媽、表妹(初子),以及舅媽的其他小孩。何以初子一家人願意走,花子一家人卻不願避難?生死之間的抉擇,到底繫乎何物?霧社事件留給我們的迷霧好像還是一片霧茫茫。
在文本沒出現的高永清,是這篇口述回憶的記錄者。他同樣出身荷歌社,族名Pihu Walis,父母死於霧社事件。他是小島源治巡查次子重男的好友,很得小島夫婦的疼愛。小島夫人就是田中千繪扮演的角色,和真實人物在長相上很不一樣;小島源治涉及第二次霧社事件警方的默許,其作為有相當黑暗的一面。高永清後來和初子結婚,成為花岡二郎遺腹子高光華的繼父。這又是另外 一個非常複雜的故事了,容就此打住。
以上用漢人的親屬概念來講賽德克族的親族關係,純粹是為了說明上的方便,和賽德克族的傳統親屬概念應該頗有距離,只有敬請讀者了解和諒察了。最後須一提的是,這篇高彩雲口述記錄所敘述的事件經過,和其他較常見的版本有一些不同,本刊用意只是將之整理出來,供讀者參考,不代表這份口述記錄的內容就是正確無誤的。
(2011/08/30增補修訂;感謝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的指正和協助。)
[1]按,比對年級,高等科二年級等於現在的國二。不過,當時能就讀公、小學校的本地人(原、漢)比例不高,若能再讀高等科,已經是學歷很高的了,擁有的文化資源與社會地位遠非今天的國中生可比。
[2]原譯稿作:「過了不久調到芦山國小(ボアルン)任教」,應是高彩雲女士以受訪當時的學校名稱來指稱當時的坡阿崙教育所,茲改;下仝。
[3]應指花岡二郎在霧社街的宿舍。
[4]這句話不是很清楚。時間順序上,推測應該是校長家廚房已經有一批人避難,但被殺死很多,高彩雲躲在屍體堆中,隨後志柿公醫夫婦也逃至該處,但志柿公醫被追趕而至的賽德克族人射殺,高彩雲目睹這一段經過。
[5]原譯文作「春陽」,是以「口述當時」的觀點敘述。荷歌社在霧社事件之後,餘生的族人被遷走後,當局將該社領域撥給都達群,戰後改稱「春陽村」。高彩雲女士口述時,可能為了讓年輕人了解地理位置,採用口述當時的名稱,而非事件前的社名。
[6]巴蘭社頭目瓦歷斯布尼,他不止是巴蘭社子部落鹿澤部落的頭目,他同時也是德固達雅(Tgdaya)群的總頭目。關於瓦歷斯布尼在霧社事件及其後的角色,見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霧社事件101問》選刊〉,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部落格,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766&next=750&l=a&fid=15(2011/08/18點閱)。
[7]一般作「番布」。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08/26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