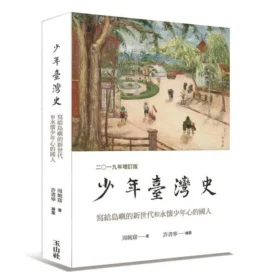開啟眼界的神學之旅
鄭仰恩

知道《面對我們的差異》(Facing Our Differences)這本書的翻譯本要出版,心裡覺得很高興。因為受邀寫推薦序,心想或許可以分享一下個人的神學心路歷程。當代盛行的神學方法論著重以個人的生命史及其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和生活處境(living situation)作為反省素材,並試圖理解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其信仰體系、價值信念、世界觀是如何被形塑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社會傳記」(socio-biography)的方法論。[1] 以下就讓我用「社會傳記」的方法來陳述我的心路歷程。[2]
三十年前的1970年代,當我還在台灣中部一所純樸、保守的國立大學讀書時,我的生活世界是相當封閉而個人化的。我的大多數同學在無奈的現實處境中選擇了行禮如儀、不問世事的人生態度,成日K書、運動、結交異性朋友、準備考研究所或出國。較具叛逆性格的同學則留留長髮、打打撞球、聽聽搖滾樂,過著群居終日、無所事事的閒散日子。那是一個心靈貧乏、單調、抑鬱、苦悶的年代!
不過,在當時的長青團契(長老教會大專團契)裡,我們卻開始接受到另一種信仰文化的洗禮,那就是從信仰的立場來思考、反省、關懷所處的台灣社會。可以想見的,這在當時國民黨威嚴統治下低壓沈寂的政治氣氛裡是相當具有顛覆性的(subversive)。試想想,當時的年輕學子十個當中至少有八個從小就是被父母告誡著諸如「囡仔人有耳無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政治好插,狗屎嘛好吃(客語)」的生存哲學。在這種情境中,我們被挑戰著開始去思考基督信仰與周遭世界的關係、上帝的主權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基督對受苦民眾的認同、上帝的形象與人權的關係等問題,也開始質疑當時台灣社會中一黨獨大、萬年國會、思想箝制、「反攻大陸」的政治神話等荒謬不合理的政策或現象。想當然的,這些看似「反社會」的思想對當時我這個懞懞懂懂的「台北囡仔」來說的確是不容易消受的,然而它也開始在我單純的心思裡糾葛、攪拌著!
最特別的是在大學三、四年級的暑假中,我有機會開始參加了當時可以說在神學思考和信仰反省上非常先進的「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在那裡,不但我的聖經觀、信仰理念,包括我的政治思考、身份認同都經歷了強烈的拆毀與重建的過程,那可以說是我信仰啟蒙的初步階段。1979年12月,就在我大學畢業正接受預官訓練時,美麗島事件發生了,這對我的信仰反省和作為「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又是另一個劇烈的衝擊!經由美麗島事件所激發的台灣史研究熱忱成為我信仰意識與本土認同的啟蒙經驗,至今不曾改變。換句話說,我被台灣的苦悶歷史經驗「重新洗禮」了!
服完兩年兵役後,我進入台灣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班。在我研讀神學的1980-90年代,歐洲的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已經從發展高峰進入圓熟階段,更進一步影響了當代最具有創造力和啟發性的兩個神學運動: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和婦女神學(Feminist Theologies and Womanist Theologies)。我特別喜歡閱讀德國三位政治神學家梅茲(J.B. Metz)、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左勒(Dorothee Sölle)的作品,細細深思「危險記憶的轉變力量」、「耶穌基督受難的自由傳統」、「不是在天上飛,而是腳踏實地於歷史與社會中的神學」、「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向終末開放的盼望神學」、「不公義始於權力的濫用」、「好的權力就是讓人得著能力」等具有挑戰性的觀點。[3] 當時,我不一定讀懂所有的神學作品,但卻深信,基督信仰必然和土地、人民的整體命運息息相關,基督徒必須盡其所能地去實現信仰所激發、喚醒的自由與解放的力量,直到所盼望的社會公義能夠成為生活中的現實。如莫特曼所言:「信仰的自由… 驅使人們從事解放性的行動,因為它迫使人們在剝削、壓制、疏離和被擄的處境中痛苦地察覺到苦難。」[4]
因此,我逐漸察覺到神學與詮釋學之間的緊密關係,我的道學碩士論文也處理了德國神學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和歷史詮釋學的主題。我發現,社會實況迫使我們對傳統的神學和聖經解釋提出挑戰,並進行新的神學詮釋。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謝根道(Juan Luis Segundo)在《神學的解放》一書中做了很好的分析。他主張,我們必須通過不斷改變中的生活現實來重新詮釋聖經,此一現實包括個人的現實及整個大社會的現實。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生活的實況不斷地在變,這個變動中的實況就會主導我們持續不斷地對聖經做出新的詮釋,這就是一個「詮釋學的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5] 這樣的循環,若能走向良性的循環路徑,那這詮釋就可幫助我們建立新的神學和新的信仰體認,讓福音真理的信息與見證能帶來人性的真實解放,而非人性的壓制和扭曲。這正是近代第三世界神學所主張的「懷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以及「意識型態的批判」(ideological critique) [6] 當代解放神學家和婦女神學家們也指出,教會本身應針對自己的神學與實踐從事意識型態的批判,釐清自己到底是在為統治者、壓迫者、父權體制服務,還是為著受迫害者、被欺壓者、無力者發出先知性的聲音。[7] 整體而言,這些具有顛覆性的神學觀點對我有極大的啟發。
在這同時,我也深刻地察覺到「想像力」(imagination)、「另類思考」(alternative thinking)或「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重要性。許多時候,信仰最大的危機就是視自己所因襲的信念為理所當然,且輕易地信以為真,絲毫不加懷疑。這種對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習以為常,甚至加以絕對化的思考方式,往往是信仰成長的最大阻礙。曾經來台灣神學院「馬偕紀念講座」演講的當代舊約學巨擘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他後來將講座內容結集出版的《另類的見證》(Testimony to Otherwise)一書中指出:想像力是「上帝帶領且轉化我們的一種精神力量,它不斷地粉碎我們的既定範疇(category-shattering),並重新形塑我們的世界(world-forming)」,它也是「上帝所賜的新能力,讓我們得以被解放,並以另類、有異於傳統的方式來透視(想像)有關上帝、世界、自我的新現實」。[8] 事實上,熟悉聖經所呈現的「異象世界」(visionary world)的人都清楚認知,聖經中的先知傳統和耶穌的福音傳統為「另類思考」提供了最佳的典範和參照點。有趣的是,這樣的觀點正反映了近五年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主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從1988年到1994年間,我到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哲學博士(Ph.D.)學位,主修基督教歷史和教理史。這是一趟既豐富又充滿驚喜的學習之旅,也是不斷邁向未知旅程的冒險之旅,不只是我的神學視野和觀點不斷擴展、深化,我也深刻體認到上帝透過「他者」(the other)對我的挑戰和啟發。這些「他者」包括婦女神學家、美國黑人、伊斯蘭教徒、拉丁裔移民、非洲人、東正教神父、各國原住民、同志族群等,當然也包括典型的美國洋基佬、歐洲白人後裔,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學生在內。在與他者對話的過程中,我的傳統神學信念不斷地被顛覆、挑戰,也被重新建構。這期間,我在神學院也認識了幾位同志基督徒,因而開始對同性戀議題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1993年,就在我正為撰寫「十六世紀法國改革宗抵抗神學」的博士論文苦苦煎熬時,美國長老教會(PCUSA)爆發了「可否為同志基督徒封牧授職」的激烈討論。該年春天,普林斯頓信仰團體裡的一些教授、牧長、學生簽署了一份名為〈普林斯頓宣言〉(Princeton Declaration)的文件,反對美國長老教會為具有同志身份和行為的人封牧授職,並宣稱他們對性議題擁有清楚的「聖經確據」。結果,神學院教授團裡的部分老師也隨即共同簽署了一份〈回應文〉,主張他們在聖經裡「卻聽到不同的聲音」。就這樣,同志議題在普林斯頓校園裡引起熱烈討論,校方也安排不同領域的教授們進行系列專講,更舉辦「同志週」,邀請同志牧師和倡議人士到校演講,並和師生進行座談、對話。當時,我就認識了這整個封牧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在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牧會的史博兒牧師(Jane Spahr)。她的信仰勇氣讓我深深感動。後來,她和著名的婦女神學家也是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的羅素(Letty Russell)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道格拉斯(Jane Dempsey Douglass)共同於1999年獲得舉足輕重的第十三屆「信仰婦女獎」(“Women of Faith” Award),可謂實至名歸。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系列演講也由舊約學教授蕭俊良(Choon-Leong Seow)編輯成書。[9]
1994年回到台灣神學院教書,也開始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參與普世運動和各種會議。在普世合一運動中,同性戀封牧問題也是眾教會關心的信仰議題。然而,不管信仰立場或神學觀點的差異,或是對封牧議題的不同見解,對同志基督徒的尊重、接納、關懷、認同卻是普世教會的基本共識。讓我舉最近參與的兩個會議為例來說明。第一個是2004年8月於非洲迦納的阿卡拉(Accra, Ghana)舉行的「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第二十四屆大會。在討論同性戀封牧議題時,一位屬於保守派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坎本(Kampen)神學院院長侯爾卓普(Pieter N. Holtrop)就公開表達:「儘管我不同意同志基督徒的神學觀點,但我卻尊重他們的基本人權,甚至願意誓死維護他們的權益。」第二個是2006年2月於巴西愉港市(Porto Alegre, Brazil)舉行的「普世教會協會」第九屆大會。會中,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不但和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愛斯基偉(Adolfo Esquivel)共同領導一場聲勢浩大的和平遊行,更在公開演講中呼籲大家致力於普世合一的必要性。他強調當耶穌呼召世人「以上帝為父」來建立一個大家庭時,所有的人都被邀請加入這個家庭:「不管是布希或賓拉登都歸屬!男同志、女同志,以及所謂的直同志都歸屬!每一位都為上帝所疼愛,看為寶貝!」他總結道:「我們只能在人性裡彼此相屬!(We can only be human together!)」想到台灣許多基督徒、牧者或是學界人士論到同志時咬牙切齒、趕盡殺絕的態度,不禁讓人懷疑他們是那一種的基督徒?
最後,我必須提到本書的重要人物之一,也就是曾經在紐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聖尼尼安(St. Ninian)教會牧會,目前在澳洲雪梨聯合神學院教授系統神學的紐西蘭籍神學家克萊夫.皮爾森(Clive Pearson)。我和他於1995-2000年間同時被推選為亞洲基督教協會(CCA)「神學關懷委員會」的委員,因此成為好朋友,也是思想和心靈上的盟友。在一次亞洲的神學研討會中,克萊夫以「不再沈默」為題分享他輔導一位紐西蘭男同志神學生的獨特經驗。克萊夫指出,長期以來,因為同志基督徒的聲音幾乎不曾被聽到過,因此,這種長期的沈默導致我們沒有機會從「他者」聽到基督的聲音。他認為,基督是通過同志主動挑戰著教會自我設定的法定界限,也讓我們重新認識那位願意改變心意、受感應(vulnerable)甚至為人受苦的道成肉身上帝。
可惜的是,自從克萊夫在亞洲基督教協會的那次分享之後,當時的總幹事腓力•卡里諾(Feliciano Carino)就四處排擠他,甚至想辦法不讓他再繼續擔任神學委員。這位腓力老兄心術不正,引發不少亞洲基督教協會同工的不滿和怨氣,後來他在普世圈子裡也一再打壓、排擠台灣,並一眛地討好中國,讓人不禁要心生義憤。克萊夫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不但互相分享神學思想上的心得,也一起關心普世基督教會所面對的處境及其議題。我們對「同志基督徒」的認同與關懷是基於相同的會遇經驗和心路歷程,也就是在具體生活經驗中和活生生、真摯熱忱的同志基督徒相遇的經驗開始的。坦白說,我所接觸過的同志基督徒大多數是既認真委身又坦誠可愛的,我在他們身上真實的感受到「耶穌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愛,以及聖靈的同在」。我也感謝上帝,讓我常常從他們身上有所學習。但願藉著本書的出版,讓更多人也能經歷到擴展視野、開啟眼界、挑戰傳統、重整信仰的心靈旅程!
[1] 在社會傳記的方法論上,我特別受到韓國民眾神學家金容福(Kim Yong Bock)和徐洸善(David Kwang-sun Suh)的影響。在數次和他們對話並交換台灣、韓國「作神學」(theologizing)的經驗時,他們一再強調社會傳記方法對建構民眾神學(Minjung Theology)的重大影響。
[2] 也請參考How I Have Changed: Reflections on Thirty Years of Theology, edited by Jürgen Moltmann and 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London: SCM Press, 1997)。
[3] Johann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Societ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0); Communicating a Dangerous Memory: Soundings in Political Theology, ed. by Fred Lawrence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7);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Idem., The Crucified Go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Dorothee Sölle, Political Theology,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Shelle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4); Idem., Suffering, trans. by Everett R. Kali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5).
[4]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p. 317.
[5] Juan Luis Segundo, S.J., 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 translated by John Drury (Maryknoll: Orbis, 1976), p. 8; 亦參Interpreting Together: Essays in Hermeneutics, edited by Peter Bouteneff & Dagmar Heller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01)。
[6] Segundo, 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 pp. 97-181.
[7] Ibid., pp. 69-96.
[8] Walter Brueggemann, Testimony to Otherwise: The Witness of Elijah and Elisha (St. Louis, Missouri: Chalice Press, 2001), p. 27. 他也舉「中世紀的經院哲學」(medieval Scholasticism)和近兩世紀的「現代性思想體系」(Modernity system)作為拒絕向另類思考開放的典型代表。亦參Timothy J. Gorringe, Karl Barth: Against-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Homosexuality and Christian Community, edited by Choon-Leong Seow (Louisvill,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