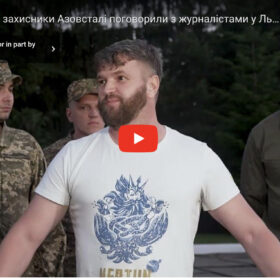海洋之子鄭成功(五)
周婉窈
我們前面說過,唐王與福王不可同日而語。福王處於尚有可為之時,卻把局勢弄得一敗塗地;唐王處於實無可為之際,仍強自振作,可批評的不多。福王有一切亡 國之 君的徵候:他寵信奸佞,恢復東廠,在南京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選淑女入宮,除夕夜還因為「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都無新聲」而不高興。唐王則大為不同。即帝位於福州,「布衣蔬食,不御酒食」,命令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深諳為臣之道的鄭芝龍,進美女十二人,唐王「留之而絕不御」,大概怕傷鄭芝龍的顏面。唐王即帝位是閏六月,第二年元旦,不受朝賀,還以三大罪自責,命令百官載罪從行。四月,生日不受賀。七月下旬局勢明顯不可為,不少官員想投降,巡閩使者截獲二百餘封的出關迎降書,唐王召集群臣,說他本不想當皇帝,但大家擁戴他,他「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糲食,有 何人 君之樂!」他「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他說他不想知道這些寫迎降書的人的姓名,當著群臣的面燒掉,希望他們能洗心滌慮,始終如一。「有 何人 君之樂!」說得多麼痛切。如果福王能像他這樣,真不知道明末的歷史是否能改寫?
唐王當眾焚燒迎降書時,其實大勢已去──兩個月前鄭芝龍已經「通於我大清」──清朝史書這樣寫著。焚迎降書後不到一個月,仙霞關不守,唐王從延平出奔,逃難時還不忘帶著十餘箱書!他和曾后於汀州遇難時,還有忠臣義士挺身護衛,情景感人。
歷史是殘酷的,南明是一部失敗史;對失敗的人,人們很少留情的。唐王能夠從錯綜複雜,如流水席般的歷史舞臺中浮現出一個清明的意象,不能不說有那麼一點真實的核心在那裡。我們今天治史者多半是多疑的、世故的,不輕易相信歷史。唐王當然有他的缺點。由於過去的患難之情,他很聽曾后的話,曾后不止參與決策,唐王臨朝時,還「垂簾共聽斷」。
當時鄭森很年輕,他和唐王很親近。唐王即帝位時,四十四歲,鄭森二十二歲,是父子的年齡。唐王賞識成功,成功顯然也相當忠於唐王。也許年輕人還是比較有理想,鄭家軍對唐王的陰奉陽違,成功應該看在眼裡,最後的背叛,終不可原諒。一九七○年代後期西方學者Ralph C. Croizier寫了一本書,提議或可用戀母情結式的詮釋(Oedipus interpretation)來理解鄭成功「殺父報國」的行為。現在這樣的說法大概不太受重視,不過,作者指出鄭成功反抗血緣父親,而認同唐王為父親∕主君,倒不無道理。從文獻來看,鄭森對父親鄭芝龍相當決絕,他不滿父親降清,也不願因父親受挾持而自己也受挾持,最後導致父親和全家十餘口因他而被處死──也就是間接「弒父」。如果容許我們有點文學的想像,或許「長身豐碩、聲如洪鐘」,恭儉自愛,對成功垂愛有加的唐王是他所追尋的「精神的父親」。喬哀思《尤里西斯》的主人翁逛了一天都柏林,結果是一場尋找精神之父的生命之旅。我們不能離題太遠,總之,鄭森對唐王念念不忘,這也導致唐王遇難後,成功不願臣事魯王(因為唐魯之間有過嫌隙),起兵後,遙奉於該年(1646) 十一月十八日 即帝位於廣東肇慶的桂王朱由榔。

清軍進入福建之後,鄭芝龍為了和貝勒王博洛相會,欲前往福州時,成功牽衣跪哭,鄭芝龍嫌他囉嗦,拂袖而起。鄭成功離開後,告訴叔叔鴻逵此事,叔叔「壯之」。鄭鴻逵接著去見鄭芝龍,鄭芝龍跟他數落成功「少年,狂妄輕躁,不識時務」。鴻逵則趁機勸他不要投降,但芝龍降意已決。由於父親要他一起投降,成功在叔叔鴻逵的安排下,率兵一旅逃往金門。鄭芝龍要去面見博洛時,招他同行,他不止不聽從,還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也就是忠高於孝,父親若不幸死亡,只好為他服喪就是了。鄭成功的這個態度在往後的十五、六年中,沒有改變過。 十一月十五日 ,芝龍帶領五百人前往福州,與博洛會面,正式降清,歡宴三天,半夜即被博洛設計挾持北上,從此再也無法回來福建。就在這個月,清軍攻入安平,成功的母親受辱自殺。十二月,成功糾合有志者數十人,揭舉抗清之旗,自稱「招討大將軍忠孝伯罪臣」。這年成功二十三歲。
根據黃宗羲《賜姓始末》,一六四四年滿人入關,長驅直入中國,打到福州時,鄭芝龍決定投降。鄭芝龍以為已經投降,有了護身符,家中未加武備,沒想到北兵打到安海,大事淫掠,田川氏亦被淫,自縊死。這件事顯然對鄭森打擊很大。在黃宗羲的筆下,鄭森反應很激烈,他寫道:「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彝法」即「夷法」,指日本的做法。不管此事是否屬實,人們想像:人子無告的忿怒,以及人子如何慘烈地「潔淨」受辱的母親的遺體。關於田川氏的記載不多,他很晚才被接到福建,是在唐王接見鄭森之後,即隆武元年(1645)閏六月之後的事。二兒子次郎左衛門不得隨行,留在故鄉陪伴祖父。田川氏在中國的時間很短,頂多一年半,最後橫遭慘禍,不能不說很不幸。
甲申、乙酉之變只是一年之間的事,緊接著唐王政權也只撐了一年二個月就又覆亡,而父親不顧他的忠告,棄明降清,母親受辱慘死,一介儒子決定舉兵抗清。史書上記載:「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枋。意氣狀貌猶儒書也。既力諫不從,又痛母死非命,迺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著儒巾襴杉,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鑑之!』高揖而去。禡旗糺族,聲淚俱并。」這是有名的鄭成功焚儒服事件。 楊雲萍 教授認為這太過戲劇化(theatrical),而懷疑其真實性。然而,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哭廟、焚儒服,在明末清初是一種社會性行為,並非不常見。焚儒服主要在作不仕的宣告;哭廟目的在表達抗議。這都是一種要引起群眾注意的作態。鄭成功的哭廟、焚儒服,可以理解成向天下周告棄文投武的決心,並宣洩國破家亡的悲情、控訴天地之不仁。
鄭成功牽衣勸止父親降清應該是在安平(即安海,屬晉江縣)。我們推測,當鄭芝龍將自己的軍力撤離延平,棄唐王於不顧,「飛帆過延平」時,成功應該也在飛帆中。鄭芝龍從打算降清開始,這個「投降包裹」裡一直包括長子成功──或許鄭芝龍隱隱約約感覺到不包括成功的降清是存在著危機的。這是鄭成功必須「遁金門」的原因。史料顯示,金門是鄭鴻逵的地盤;最後也是他退隱和安葬之地。金門離鄭芝龍老家南安石井很近,約 六海浬 ,簡直可以說一葦可渡。不過,鄭芝龍一家居住在離石井不遠的安平,因此安平是鄭成功成長之地。安平和石井屬於同個海灣線,距離很近,到金門同樣一葦可渡。
(未完待續)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08/12/22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