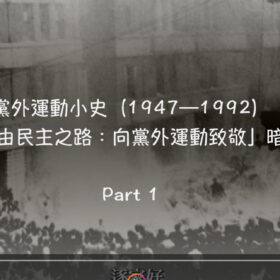以轉型正義壯大公民社會(2025共生音樂節演說講稿)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各位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站在這個台上,從當前台灣民主面對的各種挑戰,邀請大家共來思考台灣轉型正義的未來。
我想從昨天的一則新聞講起。今年是「林宅血案」發生45週年,民進黨立委范雲、張雅琳昨天舉行記者會,揭露「林宅血案」遺址義光教會因缺乏專法,無法成為轉型正義保存與活化的重要場所;而義光教會日前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市定史蹟也遭駁回,駁回的理由是缺乏法源依據,且「林宅血案」真相尚未偵破、歷史定位尚難定論。兩位立委呼籲朝野應儘速通過《不義遺址保存條例》,尤其是國民黨立委不要再拖延立法進程,阻礙社會對威權統治的反思與清算,應讓不義遺址成為推動台灣民主價值的重要基地。
我想在場很多年輕朋友或許不知道新聞中的林宅血案。1980年2月28日,台北市寧靜的巷弄內,發生了一場滅門血案。當時,台灣正處於解嚴前的高壓統治,林義雄因參與美麗島事件而被捕,家中在政府監控下卻遭到襲擊,母親與年幼的雙胞胎女兒慘遭殺害,長女身受重傷。案發後,長老教會牧師向海內外集資買下林宅成立義光教會,在流血之地播下台灣民主的盼望,教會設立已43年,一直希望能申請義光教會成為不義遺址,卻因國民黨立委阻擋《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立法,至今無法申請。林宅血案是一樁至今未破的懸案,也是台灣威權歷史的縮影。民主化三十多年了,此案真相未明,場址無法成為法定的不義遺址。45年後的今天,我們該如何思考這件事情?今天,我們擁有選舉、擁有新聞自由,但我們的國家曾經任意奪走無辜生命,儘管今天賴總統代表政府再次對家屬道歉、但至今仍無人負責,如果國家不處理歷史的錯誤,我們的民主真的穩固了嗎?
全球民主正在倒退中
我想大家都知道,當前的全球民主正遭遇空前挑戰。例如瑞典哥德堡大學的 V-Dem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V-Dem)連續第 8 年發佈全球民主報告,顯示民主退潮的趨勢,甚至倒退至 1985 年的水準,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布「2024年全球自由報告」也指出,2023年全球自由度連續第18年下降。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民主國家面臨政治極化、民粹主義、虛假訊息與社群媒體武器化等諸多來自民主社群內部的威脅。因此。可以這樣說,當前的全球民主正面臨嚴峻挑戰,在許多國家,威權勢力正在重新影響著政治與社會。
反觀台灣的民主,近年來大家都說台灣是亞洲民主國家的典範,自由之家更評比為亞洲第二民主國家。可是大家覺得今天台灣的民主是穩固的嗎?民主倒退只會發生在遠方?還是也可能發生在我們眼前?台灣的民主化30多年了,我們能確保這條民主路不會逆轉嗎?
我個人認為,台灣民主正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危機。一方面,台灣遭遇不少內部挑戰,當前的政黨極化、國家認同分裂,使得每四年我們都要擔心政黨輪替,國家是否也會被輪替的憂慮?假訊息與資訊戰滲透公共討論空間,削弱民主社會的理性基礎。而政治菁英操作民粹情緒,使社會對立加劇,削弱民主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台灣遭遇中國軍事威脅、經濟滲透、資訊戰與銳實力等全方位的侵略與威脅。當前台灣,內有政治菁英分裂,外有強敵壓境,外部侵略與內部分裂的影響力是彼此緊密地相互連動,而且相互加強,創造了台灣民主獨立的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crisis)。從去年藍白在國會選舉取得國會多數以來,我相信大家都深刻感受到台灣民主正在遭遇這種「內外交困」的危機。
當前台灣這樣的民主危機,也可以反映在轉型正義的議題。因為國民黨始終不願面對過去的威權歷史,導致去年新國會開議以來,轉型正義的工作便一再受阻。在法制方面,國民黨立委,不僅企圖透過提案來模糊轉型正義的定義,阻礙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的審議;而且,要在接下來的會期修正「黨產條例」,訂定「救國團條款」,把已經逐步追討回國有的不當財產,再奉還給救國團。這些民主倒退的提案,也都已經在藍白立委的多數護航下一讀付委。此外,藍白還已經三讀修正了「發展觀光條例」,讓本來應該在今年一月熄燈落日的救國團住宿服務,重新合法化、可以再營業五年。
而在預算方面,不僅國發會主責、用來支持各轉型正義事項的的「促轉基金」,去年被藍白聯手刪除了半數預算,想迫使轉型正義業務縮減;黨產會今年則被刪除六成的預算,幾乎無法繼續追討黨產。另外,包括內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的青年署等單位,更被以補助參與青鳥運動的公民團體等理由,遭凍結或刪除數千萬元。國民黨立委更直接點名長期在中台灣推動轉型正義工作不遺餘力的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對協會進行抹黑式攻擊,導致公務機關內部自我審查,可能不敢再補助相關活動,意圖打擊公民團體推動轉型正義的士氣。藍白聯手不僅衝擊台灣的民主發展,也重重的打擊了轉型正義的推進。
轉型正義與民主韌性
在談完台灣民主內外交困的危機,以及轉型正義工程遭受的挫折後,我們要進一步思考,除了積極投入罷免的各項公民運動以外,我們該怎麼辦?我們還要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嗎?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回到其他國家的經驗,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下一步的行動。
事實上,國際的經驗表明,面對當前的全球民主危機,避免威權復辟,更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因為,近年來「全球民主倒退現象」的研究紛紛指出,威權體制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遺緒,仍會在民主化過程中發揮實質的影響。威權遺緒不僅存在於許多正式的機構中,也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以及民間社會的生活經驗與文化之中,包括日常的政治話語和實踐。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威權體制被推翻,如果不進行社會文化變革,民主鞏固的夢想不會自動到來。以東歐國家為例,儘管經歷共黨政權的垮台,然而當公民持續保有威權懷舊的政治態度,往往容易使新興民主體制下的領導人進行民粹動員,使得公民接受那些違背民主原則的決定,進而破壞法治精神,導致民主倒退的現象。匈牙利曾是東歐民主化的成功典範,但今天,奧班政府掌控媒體、干預司法,被稱為「歐洲第一個非自由民主國家」。波蘭也曾是民主轉型的標竿,但近年來政府操控法院、改寫選舉規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已將它排除為「完全自由」國家。這些國家在 30 年前,和台灣的處境很像——剛走出威權統治,成功建立民主,但如今卻在一步步走回頭路。我們從近年的波蘭與匈牙利的民主發展可以得知,在大多數公民採取容忍的情況下,威權復辟成為可能。公民透過選舉投票給具有威權主義傾向的民粹政治領導人,這些領導人上台後透過民主程序,一步步摧毀民主。正如「民主如何死亡」作者Steven Levitsky及Daniel Ziblatt所強調的,「一個悲劇的弔詭是,民主的刺客會使用民主的制度去殺害民主,並且是慢慢的、細微地,甚至是合法地」,今日的民主之死,「通常不是一刀斃命,而是死於凌遲。」。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每個人的教育經歷來證明,威權體制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遺緒,仍會在民主化過程中發揮實質的影響。例如,最近一個重要跨國研究指出,確立個人在威權政體中的教育經驗與其民主態度之間呈現負相關。當一個人在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時期,教育內容越支持威權政體,這個人(她/他)在以後的生活中的親民主價值觀就越低。以德國為例,這份研究發現,在東德統治期間,人民多接受一年社會主義教育,對民主滿意度就會下降 4.3 個百分點,對民主支持度就下降 5.8 個百分點。這或許可以解釋,這幾年另類選擇黨(AFD)可以在東德地區快速竄起的原因,甚至在這麼短的時間躍昇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在上週剛落幕的德國國會大選中,得到5分之1民意支持(20.5%選票),是二戰以來首次德國極右派擄獲如此多的民意支持。換言之,教育不僅用來鞏固威權統治,即使威權政體已經垮台,公民在前威權政體下所獲得的教育經驗,仍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民主是否能長期支持。因此,生活在民主政治下的公民,需要學會重視民主,並體認其作為公民的角色。所以在今年1月,歐洲理事會便提出一份報告,強調在歐洲社會日益多元化、民主制度受到侵蝕、兩極分化加劇的背景下,「歷史教育」對於培養民主公民意識的重要性。報告強調「教學歷史,紮根民主」的原則,認為「良好的歷史教育」對於深入理解過去、批判性地評估現在至關重要。報告總結指出,歷史教學對於培養民主公民意識至關重要。
因此,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轉型正義」的推動與建構台灣的「民主韌性」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民主韌性」是指民主制度在面對危機或挑戰時,維持穩定與核心價值的能力。轉型正義在許多層面上直接影響著「民主韌性」的構建。例如,通過揭示歷史真相與過去的不義行為進行究責,轉型正義可以幫助重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信任基礎,為民主制度的運作提供穩定的社會條件。同時,透過強化法治和責任機制,使民主體制具備更強的抗風險能力。此外,轉型正義的教育作用提升公民對民主價值的認識和參與意識,進一步鞏固了民主的長期穩定性。
因此,轉型正義的工程,不僅是對過去的修補,也是對未來的承諾。它涉及從制度改革到文化重建的全面性工作,不僅要專注於修補過去的傷害,更著眼於透過制度與文化的變革,預防未來暴力與不正義的再現,並將民主、人權、法治的價值內化為社會核心信念,健全公民社會體質。轉型正義關注的並不是已經結束的歷史,而是我們將如何面對未來。
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台灣作為民主國家就像一棟房子,它可能在外表上看起來正常——有選舉、法院、新聞自由——但如果它的「地基」沒有打穩,那麼一旦遇到政治衝擊或危機,就可能迅速崩塌。這個地基是什麼?就是「轉型正義」。如果沒有進行轉型正義,過去的加害者仍然掌握司法、軍隊、媒體,就像地基裡埋著不穩定的結構。一旦當威權勢力捲土重來時,這些舊勢力就可能成為民主的裂縫,讓台灣變得更容易受到侵蝕。地基有裂縫,短期內或許沒問題,但長期下來,民主體系就會像倒塌的房子一樣,無法抵抗衝擊。如果我們不進一步補強這些漏洞,是否有一天,台灣會像匈牙利和波蘭一樣,民主大樓在某個政治風暴中突然坍塌?台灣是否能避免這樣的未來?
有人會問,面對中國的滲透與威脅,是否應該優先處理國家安全問題,而先擱置轉型正義問題?然而我要說的是,民主的最大防禦,不是武器,而是人民對民主價值的堅持,在面對危機或挑戰時,有維持穩定與核心價值的「民主韌性」。如果公民社會對民主人權價值沒有堅持,當中國進行認知作戰時,人民可能會對威權敘事沒有免疫力。特別是在台灣特殊的民主轉型模式,台灣的民主化是由威權政權內部啟動,導致轉型正義長期延宕,許多人對威權歷史缺乏記憶與反省。如果,社會大眾不了解過去的威權壓迫歷史,就可能對民主的價值缺乏認識,甚至對威權統治產生錯誤的「懷舊」情緒,也可能無法抵抗威權復辟的誘惑。透過轉型正義,辨識當前社會中的威權遺緒,能確保過去威權體制的遺緒不會影響現在的民主運作,讓歷史記憶成為防止威權回歸的警鐘,可以強化台灣的民主韌性。轉型正義不是萬靈丹,但它是民主韌性的關鍵基礎。如果我們不處理過去的問題,那麼當民主受到威脅時,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韌性來抵抗。因此,一個社會如何處理過去的不義,決定了它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民主社會。轉型正義不是民主的阻力,而是民主的基石。

「挖掘在地歷史運動」
因此,回到最初的問題,除了積極投入罷免的各項公民運動以外,我們該怎麼辦?最近我與一群朋友們共同發起一個「挖掘在地歷史運動」,嘗試結合「民主韌性」及「轉型正義」的理念,為建立更具韌性的民主社會提供了實際途徑。「挖掘在地歷史運動」,期待透過整合連結大學、民間團體與地方館所,建構轉型正義的生態系統,促進不同世代的對話與理解,讓公民共同參與歷史真相的挖掘與紀錄,成為歷史的見證者;並積極與國際社群合作,透過全球網絡,讓本土的經驗與聲音在國際場域被看見,共同為維護全球民主共同體而努力。
為什麼要透過「轉型正義」來連結國際社群?如同我在許多場合不斷強調的,位處第一島鏈下的台灣,台灣的民主與全球的安全緊密連結,因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確保台灣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跟臺灣在當代全球的位置有關,因此,台灣越民主,台灣就越安全。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跳脫從「兩岸關係」的架構思考台灣的未來,而是應該以「世界的臺灣」作為參考座標,一方面推動轉型正義來強化台灣的民主韌性,另一方面加強與世界民主聯盟的合作,讓民主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在此,我想邀請所有朋友們,一同行動,持續關注轉型正義的推動,共同打造民主的未來。一百多年來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台灣公民社會都在重要時刻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當前民主倒退的浪潮中,去年的青鳥運動到目前的全島罷免運動,無一例外。儘管,台灣民主之路曲折,藍白透過國會對轉型正義造成反挫,仍不會澆熄我們對於守護民主未來的決心,我們必須重整旗鼓,持續推動轉型正義來「壯大公民社會」,真正實現「永遠不再發生」,一起行動、為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奠定穩固的民主基石,作伙向光前進!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