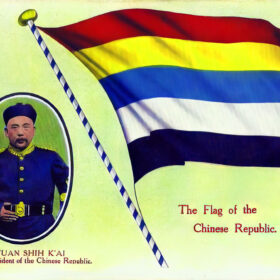「小草」怎麼從追隨黃國昌變投誠解放軍
李濠仲
近日,民眾黨因捲入京華城案的彭振聲家中變故,再次號召支持者聚集北院,一段插曲是,有個年輕人(俗稱小草)被現場主持人問及「是否會擔心要上戰場,上戰場會義無反顧地拼一次,還是希望國家考量台灣人立場再溝通?」球已經做得那麼明顯,這位年輕人卻毫不遲疑回答:「我會義無反顧投誠解放軍」,主持人立刻拿回麥克風,旁邊再有人緩頰「這不太對喔!」
「這不太對」可以有幾層意義,第一,小草的答案不是主持人要的,第二,那確實不符常理道德,任何人只要進犯台灣,當然就是侵略,只要是侵略,怎麼一個年輕人連「Say No!」都沒有就算了,還「義無反顧投誠解放軍」?
確實,近代很多例證都說明了戰爭的結束,已不是因為交戰的一方消滅另一方,而是其中的一方,認為投降比繼續抵抗更具吸引力,從而集體棄守。只是,主張以談判或非武力外交手段避戰是一回事,視反戰為唯一信仰是一回事,在任何道德中,直接「義無反顧投奔侵略者」,無疑相當反常,尤其發生在年輕人身上,而這樣的年輕人,則存在於號稱廣受年輕人支持的民眾黨。
很顯然,跳過避戰、反戰,直接投誠敵軍,恐怕已不是來自對戰爭的冷漠或悲觀,而是徹底「自我貶值」的結果。至於自我貶值從何而來,照諸多心理學分析,雖然多數情況下,人們會選擇相信「真理將使人自由」或「正義將得到伸張」,只是一旦它沒有立刻被兌現成真,這就會讓其中一部人感到幻滅,然後反過來貶抑這些價值觀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即自我貶值。18世紀以來,它另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用詞──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的表徵複雜,否定「既有價值觀、道德感」是其一,它和政治行為的連動,大者,有了無政府主義,小者,就是不相信自己可藉由勤奮努力去克服眼前艱難,乾脆躺平,但結果常是讓自己既感到自由,又同時感到沮喪。英國慈善機構「國王信託基金」2022年有份針對後疫情時代的調查,發現其中位處最年輕區塊的「Z世代」,正是所有年齡別中,最無法從疫情恢復過來的族群。也就是說,當下虛無主義在年輕人身上,確實又更顯著。
因為年輕,所以虛無,因為不相信自己,所以自我貶值,因為自我貶值,所以「義無反顧投誠解放軍」,這一串似乎就有了連貫。但年輕人一定容易心生虛無?這或許要從另一個方向解釋。
2019年,《商業內幕》給出一份民意,發現大多數Z世代既不認為自己是保守派,也不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主要因為他們對什麼都不確定,或以為凡事隨時都可能幻滅。無可否認,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個世界都面臨了一個更模糊的未來,這必然加劇了Z世代此一心理,不過,隔兩年,Common Sense Media就提出了更具體的解釋(顯然這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課題)──虛無主義最活耀的一代是「Z世代」,而「Z世代」正是最仰賴社群網路作為溝通、媒體消費和資訊發現的一代。簡言之,長期沉浸於資訊過剩的數位回聲室,已導致「Z世代」更容易走向虛無。
根據Common Sense Media的調查,平均而言,青春期前的青少年每天在電腦、手機螢幕前花費約五個半小時,13到18歲青少年,每天花費約八個半小時上網。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瀏覽Instagram、TikTok、Twitter(現在的X)和YT,以及更為顯著的是,比起其他世代,他們連Google搜尋都放棄了,而是完全仰賴各類社群平台的強大演算法,看到什麼就以為什麼。
其影響就是,「Z世代」也是最容易受到曲解訊息、假訊息,以及極端主義言論左右的一群,進而,當諸多假的、扭曲的、片面的訊息在這族群間反覆被分享、傳送,一個人先是批判推理能力被弱化,繼之,連基本信念、道德都可能遭到瓦解。因為這個過程不只不會讓人拓展視野,還會大為限制一個人接觸多元觀點,從而對世界的理解愈形窄化(甚至扭曲),結果是輕易否定任何可能性,當網路世界和個人現實環境愈不匹配,虛無主義便得以萌芽。
去年此時,當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身陷京華城容積率案,明明各方辯證很多(對柯有利不利都有),非常「癡迷」直播的黃國昌卻大肆鼓勵支持者「剪掉有線電視線」,說「看我的YT,半毛錢也都不用收」,希望支持者統一接受他的論點和詮釋。然後,一年過去,當民眾黨又為了柯文哲集聚北院,便出現了那位「義無反顧投誠解放軍」的「小草」。這就有了鎖定直播、沉浸回聲室、而後虛無主義生的組合餐味道。
更大的問題是,2018年劍橋大學出版一篇題為「投降在戰爭中的傳染」論文,結論之一為:投降在戰鬥中具有群體傳染性。那麼,當「義無反顧投誠解放軍」一出口,儘管現場主持人馬上搶回麥克風,另一主持人急忙說「這不太對喔」,如此意識,又是否在「小草」間早就傳染開了。
(轉載自:李濠仲 2025/7/3 臉書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