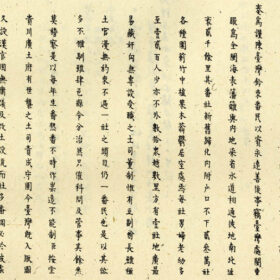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紀念鄭南榕 2009年4月7日)
黃文雄

我們今天在這裡一起懷念Nylon,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非常複雜的心情和感慨,尤其是當我們想到他那壯烈的最後抉擇,以及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肩膀上的責任的時候。
我自己是在1989年一月底聽到Nylon被傳訊的消息的。那年正是我海外流亡的第18年。我還記得大致的日期,因為接到同鄉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正好和一群外國朋友,在為兩位即將回國為民主奮鬥的東歐朋友開惜別會。那幾年正是共產專制世界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期,而台灣的專制獨裁體制也開始鬆動。前一年強人還沒有指定接班人就去世了。這件事固然埋下國民黨分裂的種子,也是蔣經國對台灣最後的貢獻;但是,政局也因此更充滿不確定性,更加難以預測。如果當時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頭頭,能夠克服他們各自的野心而合作聯盟,李登輝將沒有可趁之機。最後的結局,會不會還是蔣經國去世前幾年所設計的開明專制:開明是比較開明,專制還是專制。
這是我當時的憂慮。這是一個極端關鍵的時刻。在這樣的一個時刻,聽到Nylon那一句「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會抓到我的屍體」,頭殼裡浮起他在辦公室準備的那三桶汽油,心中受到極大的震撼。以後的七十幾天裡,我每天起床,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Nylon。在1970年刺蔣之前,我有半年的時間,反覆分析過做那件事的價值和策略的問題。Nylon是一個受過哲學訓練、喜歡分析反思的行動家。我相信他說出那句話之前,也一定經歷過類似的過程。
價值和策略。也許會有人不習慣看到策略被拿來和價值並列;其實,不論所堅持的價值有多崇高,事先竭盡自己的能力,計算行動的可能效果和後果,只不過是負起起碼的責任而已。可是在前面所說的那個關鍵時機,Nylon面對的情勢,可遠比我當年所面對的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ultra-stable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至少有一段時間,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可是1989年Nylon所面對的局勢,就比我在1970所面對的複雜多了。美國這個大老板為了打擊共產陣營而「聯中制蘇」後,連聯合國席位都保不住的國民黨這個小伙計大幅貶值,對美國的價值幾乎只剩下台灣島的戰略地理位置而已。KMT被迫在國內開始鬆綁。雖然前景還是渾沌不明、充滿危險,但這一程度的鬆綁卻也包含了不少政治和社會改變的可能性。Nylon在堅持原則與尊嚴之餘,還必須去保護當時那些已經打開或可能打開的可能性。這一切都比我剌蔣前所面對的複雜困難多了。所以1989年那七十幾天,我每次想到他的處境的艱難,心中都難以自抑的充滿了兄弟般的痛惜,以及仰之彌高的尊敬。他壯烈的自我犧牲後,就更不用說了、
不錯,Nylon是可以不公開說出「國民黨不能抓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那句話,而到法庭和監獄裡繼續他的抗爭(很多愛惜他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經如此希望)。但是話既然說出來了,一定有他的理由和計算。如果我的猜測沒錯,他的推理應該是這樣的:既然更激烈的行動只可能給國民黨暴力鎮壓的藉口,那麼他就付出自己的生命,佔據道德的高地。這樣做,既可以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尊嚴,也可以保護前面所說的那些已經和猶待打開的可能性;既可以打擊日趨一窮二白的蔣家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也在當時仍然上下升降的政治局勢的天秤上,在自由、人權、民主和台灣主體性的這一端,放下他個人的砝碼。這種自傷以傷敵的壯舉,需要多麼堅韌的道德勇氣,以及多麼清明的效果和後果的計算!國民黨那些人一定無法想像這樣的台灣人,可是Nylon卻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的確有這樣的台灣人。這是Nylon留給我們的永遠的遺產。
我們還活著的人現在所面對的情勢,事實上並不比Nylon所面對的容易。一方面,我們有更多的民主和人權的成就──不要忘了這是Nylon幫助我們獲取的成就──需要去珍惜、衛護、擴展、深化。另一方面,在兩大強權的夾縫裡,我們還要面對國內和國外的各種反動勢力。我們的責任和工作並不比Nylon輕。時間有限,我也沒有能力提出全面解決的方案。我只想告訴大家,我希望明年的今天可以送給Nylon的一個小禮物。
最近幾年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挫折感,有些人難免對人權的爭取和民主的深化,多少失去了信心。例如去年11月陳雲林離開台灣後,在一個聲援野草莓的場合裡,就有幾位「衝組」對我埋怨說「這些學生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嘸夠勇」。我們因此展開了一場討論。
我大概是這樣說的。我說,各位在11月6號那天有沒有看到學生在行政院靜坐抗議時被警察抬走?兩個警察服侍一個學生,百來位學生花了警察多少力氣?這些學生不過在前一天晚上聽了一場非暴力抗爭的演講而已,並沒有受到完整的訓練;多數人沒有完全把身體放軟,有的人被拉起來就自己走,有的人被抬到警備車門口就站直了,自己上車。我在美國的時候參加過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反核武運動的非暴力抗爭。我知道如果完全把身體完全放軟,或一路到被放在車上的座位之前都拒絕合作,政府所必須動員的警力將更多出很多。然後想像和計算一下。根據警政署的統計,陳雲林來台那幾天總共用了一萬七千多人次的警力。如果那幾天出來抗議的人都受過嚴格的訓練,警方必須調派出多少倍的人力?如果那天是一萬人的莊嚴的靜坐,會給陳雲林和中共當局,還有我們自己的政府,什麼樣的台灣人民的教訓?搞不好消息傳到中國,海峽那邊可是每年都有幾萬場抗議,而且越來越多。不只這樣,中國的統治集團會不會開始想,即使用武力一口吞下了台灣,要怎麼解決消化的問題?
這是一個深具鄭南榕精神和方法學的例子。要做到這樣,需要有價值的堅持、思想的武裝、效果的計算,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紀律。我沒有時間向大家報告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運動以及平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se)的歷史、經驗、技術和理論;有興趣的人可以上(例如)Gene Sharp所主持的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網站。我也沒有說,這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我只是想用它來舉例說明鄭南榕的勇氣、智慧和方法學,以及他對公民社會自我組織培力的重視,並且向Nylon這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說:我已經在和幾位影片製作者商談了,希望能製作一部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歷史、理論和技術的教學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掃墓時,可以用來代替鮮花,向你致敬。
請你安息,Nylon。我們會努力各自而又一起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
謝謝菊蘭和竹梅,也謝謝大家。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2/04/19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