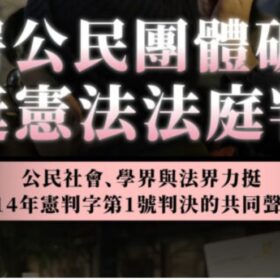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陳怡凱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 (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 (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 (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 (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 (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 (p190)。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 (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 (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 (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 (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 (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 (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 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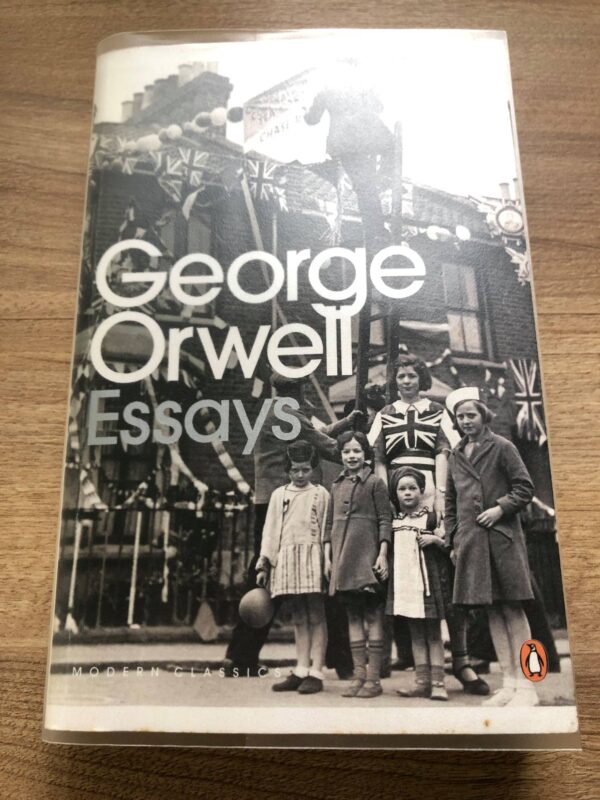
(文章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20/10/12 臉書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