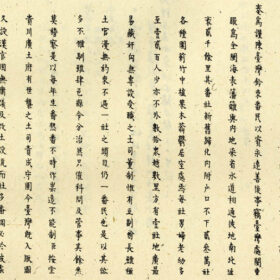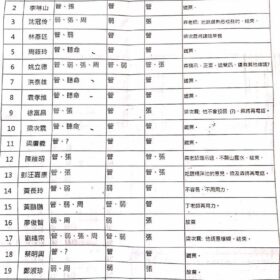訪鍾逸人、 李喬 先生(舊文新刊)
林易澄
這次拜訪鍾逸人先生與李喬先生,帶給我不少省思。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中部地區民間武力的二七部隊,便是由鍾先生主導,他並將過程詳細地寫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裡;李喬先生則以此題材寫有大河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這兩本書對當時事件的記憶與重述,在內容與形式上,都使我們對近代史有更多的思考。
七月下旬的一個禮拜天,一早我便跟著周婉窈老師與其他同學前往彰化北斗,下午又趕往苗栗公館。這兩地以前都沒有去過,給我很深的印象:隱於鄉間,與鍾桑性格同樣豪爽的美式住宅,以及李喬先生門前的丘陵、水田,只是半天行程,卻已經與臺北的城市生活相當遙遠了。這也像是提醒著,只從書面上讀過材料是不行的,必須要實地進去走過一遭才能了解這些歷史體驗與記錄本身產生的過程與意義。

一、Butaichō
部隊長每一次回答的時候,說的內容幾乎跟書上是一模一樣的,連句子都不差,好像那本上千頁的回憶錄就放在手邊一樣。(我背包裡倒是有一本)。不像其他拜訪過的長輩,常常會說到一半停下來,在記憶裡揀選翻找合適的表達,排列事件的先後順序,一點一點勾勒出多年前的那些面孔;部隊長的故事卻是清清楚楚的,彷彿一甲子前陽光的溫度還貼著他的臉:「我到了旅館,謝雪紅問我的名字,把我帶到窗戶前面,就著日光打量我的臉。她說你該叫我什麼,我說歐巴桑。她說不對,要叫阿姨,不過歐巴桑也可以啦。」
我們幾乎不用準備什麼問題,他就會一直往下說下去。或者說準備的訪談草稿其實也派不上用場,不管原先的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直接回到自己的故事裡。
本來有些失望,後來問他記憶力怎麼這麼好,他回答說,在牢裡十七年也沒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又好像理解了一點。
以前對部隊長的印象不是太好,看過幾位當時戰友對他回憶錄的質疑,覺得是一個容易誇大,逞英雄氣的人。這次聽他把裡面的事情又講了一遍,那神情語氣倒不像是刻意去吹噓標榜,而是他自己便這樣相信著。
我知道他在軍監裡過得不是很好,因為目標、信仰和大多數的政治犯不同,一直被孤立排擠,對這樣的日子來說,或許編了又織,織了又拆的回憶,是他少數的寄託吧。
從二十六歲到四十三歲,他用了十七年的時間去回憶那半個月的事情,就著被捕以前片段的資訊,試著用殘缺的碎片拼出一幅輪廓來。(那終究是個一片混亂,情報、消息、流言與官方說法纏成一塊的半個月)
那故事便一遍一遍地重塑成形,有了自己的生命,變成我們那天聽到的樣子。那支幾百人的武裝,在那裡面,也成了幾千人的部隊,距離歷史曾經可能的轉變,只差一點點而已。
這樣,部隊長便成了一個有些可愛的人了,這樣說絕對不是因為他帶我們去的那間肉圓非常道地的關係。
二、反思
身為一位歷史學的研究生,這次拜訪一開始是抱著「究竟事情的真相是什麼?」的想法。希望能重新檢視二七部隊的一些迷團,諸如:編制、人數是否有所誇大?跟左翼有關連的成員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隨著一天的行程走下來,這個想法慢慢有些改變。
在先前閱讀過的資料中,將該部隊視為紅軍的說法, 和鍾 先生在回憶錄中的陳述,兩者有相當的差異。不過兩種說法卻也有相同的地方,它們都顯得太清楚而有條理。《辛酸六十年》裡,描寫戰後到二二八這段時期的臺灣社會與地方形勢都極為細緻,但是到了二七部隊的段落,卻給我一種歷史演義式的故事感。只見到鍾桑四處奔走,主軸看似清晰,但是事情與事情的連續因果卻充滿空白與隙縫,全賴鍾桑發揮說故事者的優秀才能,將之串連起來。
原本早上見到沈浸於自己回憶錄中的鍾桑,想大概就到此為止了吧,但下午到了李喬 先生家裡,因為他們的私交,李喬反而可以沒有顧忌地提出一些尖銳的質疑,也間接修正了我原本的想法。由於時間的關係,李喬的質疑只有點到為止,並沒有真的釐清二七部隊的樣貌,但給我最深印象的,不是李喬的提問和鍾桑被質疑時的反駁,而是鍾桑的樣子。在遲疑之中,並不是他發現自己的敘事被揭穿了,而是他也停下來,像是發覺自己之前並沒有完整思考過那些提問。然後重新回到那個時間點,試著在有限並且不可靠的資訊中,重新把事情整理出來。
我想起Sewell分析法國大革命的那篇文章,他根據時日,一點一點地重建了巴士底監獄攻陷前後的巴黎,勾勒出一個事件如何在發生之後,被傳播、詮釋,而從一個偶然的意外變成最具影響的關鍵。[1]如果我們能夠回到歷史事件的現場,我們將會發現手上不會有清楚詳盡的結論,不會有預定的方向,從各方得到的資訊總是混亂、可疑、片段,就像是被包圍在大霧之中。(在資訊流通管道遠遠進步的今天,颱風過後的幾天人們仍不能全面掌握災情,更不用說當年了。)

這片混亂模糊,也許是我們重建歷史的前提。它和當時的行動、日後的敘事緊密交錯在一起。它先是成為歷史行動者做出抉擇的處境,然後這些抉擇與行動又影響了日後的道路,生產了種種挾帶後見之明的敘事。這裡甚至不僅是勝利者的敘事,也包括受挫者的敘事。在日後,源於對失敗原因的追溯,一步一步地試圖找出歷史曾經有過的某個可能性,賦予那模糊的大霧一個較為清楚的樣貌。 重要的不僅是實情究竟為何,也在於從眾多片段編織成完整敘事的過程。並不是去指出某個故事某處細節加以質疑,而是藉由敘事中引致疑惑的點,重新回到那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空。同時在回溯的過程裡,去理解故事怎麼變成後來的樣子。
近來我對嘉義地區民軍的參與者,作了一些訪談,從此地的情況推想,二七部隊當相去不遠。它也許更接近各志願小隊林立的集合體,在其中,太平洋戰爭的軍隊經驗與民間動員體制或有幫助,但恐怕難有鍾桑筆下紀律號令嚴明,成體成系的建制。如果有更多的時間可能會有改變,但是在短短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裡,那些編排建制或許不少是日後的回溯。紅軍之說的可信度當也相近,儘管許多臺中地區參與二七部隊的年輕人和學生,與日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有所牽扯,但是就目前所知,在二二八前後地下組織的開展仍然很稀薄,這些成員的左傾恐怕不是二七部隊之因,而是二七部隊之果。
或者可以說,日後的種種敘事,都揭示了那個模糊不定的時刻裡,某個歷史道路的可能性。反過來,這些敘事也做為指引,引領並要求我們回到那個時間點,去理解當時的複雜性。特別是二七部隊的相關資訊能夠公開談論,又是在被封印了多年之後(是這個意思嗎?),它的歷史也包括了日後這段漫長的時間。
這樣,如果有機會探訪當時參與的行動者,便有許多問題想要請教。例如,「二七部隊」對參與的人們來說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它的建制與成員、小隊之間的關係為何?參與者如何理解自己的行動與組織?它提示的方向與可能的未來是什麼?當時如何思考所謂「國家」?沒有參與的關係者如地方士紳,又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我想,那可能會是一份各個不同的資料,有的全面有的局限,有的往這有的往那;也許對抽象概念的理解會是樸素的,甚至是拼湊的;也許從中會看到日後敘事的原型,又或者在所謂的「口述」中,日後的敘事反過來影響了事實的原貌,而又留下歷史地層的痕跡。
如此,當我們伴著那片模糊混亂一路走過來,或許便能較好地去理解,這一個一個有長有短的敘事,以及它們日後被形塑的過程,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所謂的歷史的「真實」,並不僅在於這些敘事是否完全經得起材料與事實的驗證,也在於用這些殘缺不全的材料所陳述的故事,折射出的光影。同樣的碎片資訊,不同的人們如何編織成自己的故事,這個過程透露出參與者的心態與思維(有普遍的,也有特殊的),哪些事實對他來說是重要的,以至於從事實(fact)變成事件(event),以被編織進敘事裡。
從這個觀點來說,鍾桑雖然不能說是一位好的史家,卻是一位優秀的「說故事的人」。對於歷史的研究者而言,關於那個時代的,優秀的「說故事的人」,是非常值得細細探究的。這樣,對於年底要出版的回憶錄第三集,也就倍感期待了。
註釋
[1] William H. Sewell,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1996, pp.841-881.(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09/10/26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