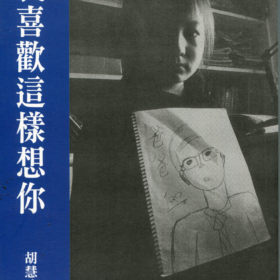沒寫完也寫不完的懷念──記Benedict Anderson
黃文雄
(原稿撰於 2015/12/24)
因為剛逃過另一次小中風,又碰到眼睛黄斑部病變惡化,即將動眼科手術,這篇短文只能記下Ben首次訪台、也是我們首次見面時的兩件事。(編按,Ben即Benedict Anderson教授,Imagined Communities〔中譯《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1936年生,於2015年12月13日過世)
我在1965年從匹玆堡大學轉學到康奈爾,和Ben同為研究生。雖然因為Cornell Papers事件久聞他的大名,卻無緣相見。在康大一場大型反越戰活動後的啤酒聚會上,我倒是和他的老師George Kahin談過話,談的是蔣家政權在越戰中的幫凶角色。Ben說他那時應該是在湖邊大草坪上的另一角。
這一錯身而過,真正見面時已是2000年。
《想像的共同體》初版的中譯本已在1999年出版,幾乎是出版周年的時刻,Ben應國策研究院和文建會之邀來台訪問並在中央圖書舘演講。出書的時報出版社的朋友邀我和他一起吃晚飯。十五年了,老年人記憶不好,我只清楚地記得晚宴或稍晚之後的兩件事。
第一是談到Ben的著作的時候,我提起一位泰國「僑生」朋友。很多人不知道台灣來過一群很不平常的「僑生」,其背景是:不少華僑家庭的成員加入了東南亞的社會主義運動,難免有人因此被處決或遭受其他的迫害牽連,當時的台灣因此被認為是送子女留學最「安全」的地方。這些僑生中有些人其實有些直接間接的運動涉入,對KMT統治下的安全警覺以及一般的政治成熟度,比我當學生時那個鎖國時代的台灣年輕人高多了。“Emile”(他和我一樣,書寫外文名字時都加引號)就是其中之一。因為有他信得過的人介紹,和某些在國際學舍認識的美國朋友一樣,他成為我禁書的來源和政治認知上的好友和益友。
1998那年是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周年,我應邀代表台灣到巴黎參加國際人權界和UN合辧的「人權衛護者高峰會議」(Human Rights Defenders Summit),因為偶然的因緣知道他也在巴黎。見面後同床談了一整夜,才知道他為甚麼自我放逐於巴黎。原來他回泰國後參加了反軍方獨裁的民主運動。很多泰華策略性地採用泰國姓名,他家也一樣。但到他這一代,不少人已經自認是泰民族的一員了。1976一次政變後的屠殺裡,他掩護幾群左派學生逃到山上泰國共產黨的基地。可是在山上的兩年裡,毛派的泰共和這幾百個學生談不攏,甚至不知道如何相處。當時的軍人總理很聰明,宣佈大赦,讓這些學生回家,泰共也樂得把他們送走。如”Emile”他們所料,因為柬埔寨──越南──中國之戰爆發,泰共被中共出賣,失去了許多境外(包括中國雲南的)基地,從此衰敗。鄧小平後來還風光地訪問曼谷,成為太子加冕典禮上的國賓。“Emile”回到曼谷,和其他某些上過山的泰華子弟(有人叫他們「紅色資本家」)一樣,想從家族事業出發,替勞工階級做些事,卻因此和父兄伯叔因此失和,健康又不好,乾脆自我流放到巴黎來。
我會跟Ben提到“Emile”,部份原因是“Emile”前一年剛剛病逝,同時也是因為我知道Ben在《新左評論》對這段泰國史有過鞭辟入「裡」的分析(該文後來收入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第八章)。我猜他應該會想知道他所分析的歷史中某個個人的遭遇。他果然非常關心。但這裡才是我想講的重點:他問了許多有關“Emile”的事,從情境到心境,從同理到同情,有些問題我自己都沒想到;可惜沒有、也不可能把它錄音-不,應該是錄影──下來。我想起醫者終極理想的「客觀之愛」(objective love),內心有無比的感動。我有個感覺:透過”Emile”的連結,Ben和我是在那一刻成為朋友的。
我想應該是這份感動,讓我知道我可以跟他提另一件事,也就是救援蘇建和等「汐止三人」(國際人權界通稱的Hsichih Trio)。
刺蔣案後,我棄保走入地下,經歷了二十五年的異國流亡,1996才潛返台灣,之後參與觀察了兩年留美和流亡時都在見習參與的各種社會運動。1998年台灣人權促進會選我擔任會長,2000年四月是我最後一任的末尾。「汐止三人」這個冤案已經糾纏九年未決。各種方法都用過了,唯一的辦法似乎是全案再審。這就必須對政府另有施壓的策略。我想到的辦法是定時定點的靜走,不論要走多久。靜坐和靜走(vigil)有宗教的根源,我和台灣神學院的朋友商量,又找林永頌長老/律師幫忙,選定正好在立法院旁邊的濟南長老教會,和人本基金會和司改基金會合作,風雨無阻地靜走了214天。靜走從四月十五日開始,Ben來台時正在進行中。
我給Ben作了蘇案的簡報,邀他参加我們的靜走。他果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不但如此,那時陳水扁己經當選,李登輝幾周內就要缷任,他開始和我討論這兩位總統邀見時他能做些甚麽。最後的結論是,李快卸任了,包袱較小,不無赦免「汐止三人」的可能,不妨一試。於是他就以他和李都是康奈爾校友的身份寫了一封信,在總統府當面遞交。當然,他最相信的還是人民的力量。四月二十七那天見過兩位總統之後,這位以天龍國的標準而言有點不修邊幅的國家貴賓,就趕到濟南教會参加人民抗議的行列了,創下至今還沒人打破的國賓訪台先例。
這種行動是Ben常做的事。例如,如果你知道他在研究印尼的同時也收養了兩個印尼孩子,也許就不會感到驚訝。


雖然這些事值得寫,我絕對無意把他刻畫成人道主義者。因為我知道如果他還在,如果他會看中文,而我又這麼寫,他會皺起眉頭,翻到吳豪人那篇〈全世界的青蛙們,聯合起來〉。如果他還在,我寧可講忘了跟他說的另一個刺蔣案笑話 (該案發生後,政大把我從校友錄除名。有人向該校抗議。學校的回答是:本校畢業生射擊成績不及格者,一律除名!),搏這個老頑童捧腹一笑。就像他的《想像的共同體》,Ben就是Ben;他不喜歡被歸類,也是無法歸類的。
既然沒有力氣談他給我的言教,最後,我只想跟Ben說:
幾次想念你的時候,曾經自私地想以泰國monsoon雨季太長為藉口,把你偷到台灣來,或者到叡人工作所在的中研院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或者到你喜歡的東海岸上的東華,或者到冬天仍有暖陽的古城台南,或者在三地間隨季節遷移(這應該很合你的胃口)。這樣,我就可以較常聽到你那佻皮的笑聲和智慧;而且,我相信透過你的身教與言教,只要帶出幾個博士生來,在某些在台灣不受重視但卻因而更重要的面相上,假以時日,台灣或將會是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我人微言輕,事情本來就無進展,現在這個夢想是鐵定無法實現了。我只小你一歲,到時候就循着你的笑聲,去找你聊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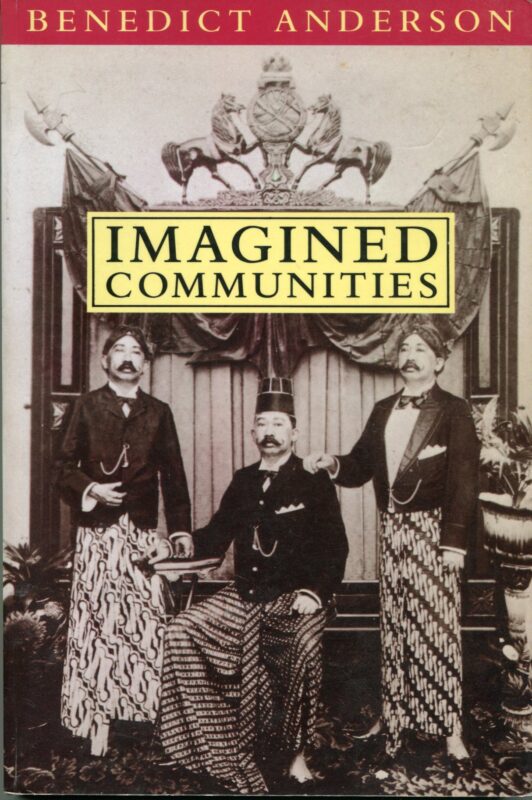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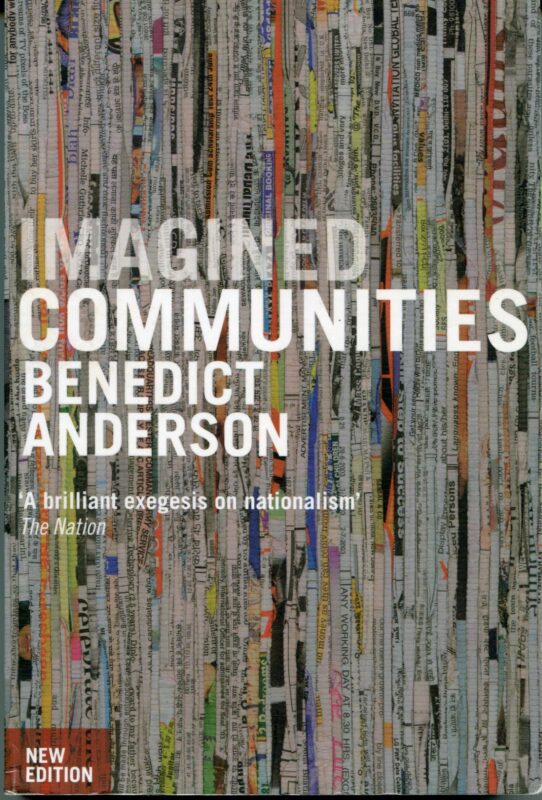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2/06/27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