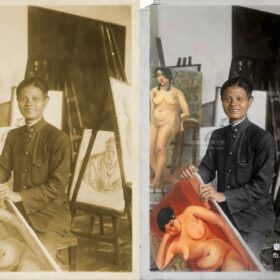基督福音與原住民文化的會遇:
聖經「蛇象徵」與排灣族「蛇圖騰」的對話*
曾宗盛
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探討聖經的「蛇象徵」與排灣族的「蛇圖騰」兩者的對話與融合, 說明從積極正面的角度來看待聖經的「蛇象徵」以及傳統文化的「蛇圖騰」,可以讓福音與文化產生巧妙的融合,展現具有排灣文化特色的聖經詮釋與信仰表達。本文特別以屏東三地門長老教會及台東土坂天主堂內部設計為例,說明文化瞭解及聖經概念彼此相互影響,帶來福音與文化之間循環的互動關係。筆者主張原住民文化與基督信仰可以彼此深化,相互提昇。本文結論強調,從新的觀點來瞭解文化以及詮釋聖經,可以讓我們對福音與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與委身。
前言
蛇圖騰在排灣族傳統文化中是個重要的象徵,它代表這民族的生命起源文化傳承、與身份認同。當排灣族人與基督宗教相遇之後,醞釀宗教觀念的轉換。不少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族人對傳統蛇的圖騰產生不同的態度,蛇不再是身份認同的象徵,而是魔鬼的記號。這巨大的轉變對排灣族信徒在面對自己既是基督徒又是排灣人的雙重身份時,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困擾。福音與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此展露無疑。〔1〕
今日排灣族基督信徒如何看待這傳統的蛇圖騰呢?我們能否在過去的模式(認為福音與文化互不相容)以外,找尋其它可能的整合模式呢?本文以「基督福音與原住民文化的會遇:聖經「蛇象徵」與排灣族「蛇圖騰」的對話」為題,為基督福音本色化的議題作一個案例研討。期盼在福音與文化互動之間,找尋一個相輔相成的可行路徑。
1、蛇圖騰在排灣族傳統的意義
在排灣族的文化傳統中,蛇佔有重要的地位。蛇是祖先,民族生命的來源。在排灣族民族來源的神話裡,流傳著不同的始祖創生傳說︰有太陽卵生說、蛇生說、石生說與壺生說等。〔2〕許多部落流傳不同版本的「蛇生說」故事,包括蛇蛋生祖先、蛇生人、或蛇化成人等。這些神話故事又都與排灣族貴族/平民家族來源有密切的關係:〔3〕

(1)齊阿齊考社:
流傳「蛇孵化太陽卵」的故事︰很久以前有個考加包根山,太陽降臨在這山頂上, 下了一個紅色與一個白色的蛋。一條名叫保龍的靈蛇孵了這兩個蛋,結果孵化出男女兩位神。男神名叫保阿保郎,而女神名叫查爾姆嘉爾。這兩神的後代就是頭目家族。至於平民的祖先則是由青蛇的蛋所孵出的。
(2)佳平社(Kaviyagan)︰
很久以前有洪水來襲,淹死了所有的人與動物。當時有一神靈入山時發現蛇蛋, 仔細一看,蛋裡面有人形的影子。後來蛋殼破,人出現,這就是排灣人的祖先。
(3)古樓社(Kuljaljau)︰
很久以前 Amawang(萬安社)有一位女神。有一天她在盪鞦韆時,盪得太用力, 結果鞦韆斷了,於是她掉進地下的洞穴裡去。後來從這洞穴中出現另外一位女神,住在這一部落,後來她與瑪家社人 Pulaluyaluyan 交往。有一天 Pulaluyaluyan 口渴,女神就出去提水。歸途中她撿回了一枚百步蛇蛋與一枚龜殼花蛇蛋。過了不久,百步蛇蛋孵出頭目家祖先,而龜殼花蛇蛋則孵出平民家祖先。曾經這兩家族通婚過,結果生下的孩子只有一個鼻孔與半個嘴巴。因此後來頭目家與平民家之間禁止通婚。
(4)牡丹社(Botan)︰
很久以前在大武山上,有一根竹子裂開,生出了許多小蛇。蛇成長之後就便成了人,這就是排灣人的祖先。
(5)Atsudas 社︰
很久以前在 Pinabaokatsan 有一根竹子。竹子裡出現了靈蛇,化成了男女二神。這兩個蛇神生了後代,就是人的祖先。
流傳各處的「蛇生說」故事,說明排灣族各部落對蛇心存極大的敬意。特別是面對百步蛇時,更是流露深深的敬畏之情。這種情懷表現在排灣語稱呼百步蛇的名稱上面︰Vulung(元尊/大拇指)或是 Kamavanan(本尊)。此外也展現在排灣族人自我的身分認同當中︰百步蛇的圖騰成為排灣族的象徵,不論在食、衣、住、行、舞蹈、娛樂,或是任何角落處處可見(雕刻、繪畫、刺繡、建築)。〔4〕
在現今排灣部落的生活中,百步蛇仍是值得尊敬與敬畏的「老朋友」。在任何地方看到蛇的時候,族人一定要對牠說話:「對不起,打擾了」,或說「對不起,我剛好經過這裡」。甚至在山上小路遇見穿越中的小百步蛇,也要對牠說「請你先走」。台東達仁鄉土坂(Jua-ao)〔5〕頭目(Bajalinuk)祖靈屋裡的祖靈木雕像(百步蛇、雙頭百步蛇、與部落祖先),足以說明百步蛇、祖先與現今族人之間,密切的生命關連。
除了百步蛇做為排灣貴族祖先的象徵以外,龜殼花則做為平民階層的祖先象徵。雖然貴族與平民有社會階級地位及權利義務的不同,分別用百步蛇或龜殼花來區別彼此的差異,不過蛇做為祖先的象徵記號則是一致的。在排灣族的生命觀裡面,百步蛇/龜殼花扮演重要角色,至今許多族人相信,祖先過世之後,並不是消失,而是化為蛇,繼續生活在這世界中。〔6〕換言之,排灣族部落、家族與族人生命的傳承,都連結在蛇與祖先的身上。因此我們可以做以下的小結︰蛇圖騰象徵排灣族人的生命來源、自我認同與文化傳統。它也清楚展現在族人的生活、藝術、與宗教中。.
2、當排灣族遇見基督宗教
排灣族與基督宗教的接觸是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事。日本統治台灣期間(1895-1945),日本人強迫原住民信奉神道教,神社的設立則破壞了原住民族傳統的宗教與社會制度。而強迫學習日語,更造成原住民族文化傳統斷絕的危機。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殖民五十年的台灣。同時也結束了對原住民族長達二十幾年的「理蕃政策」,原住民得以再次和外界接觸。排灣族三地門部落頭目向漢人牧師詢問:「今後我們要敬拜什麼神?」開啟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7〕長老會原住民牧師酋卡爾從宣教史的角度對此新接觸做了以下的評述:
「『今後我們要敬拜什麼神?』此一問,隱含著排灣族原住民對祖傳信仰的失落,或說當時很多人已經因為被迫的緣故信奉神道教,因此日本敗退之後因理不出回歸祖傳信仰之途,故而尋求另一個宗教。」〔8〕
時代局勢為排灣族戰後接觸外來新宗教鋪路。從某方面來說,基督宗教與排灣族的對遇,填補了族人宗教心靈的空缺。最早傳入排灣族部落的基督宗教有基督長老教會(1945西排灣/1948東排灣)與天主教會(1950),以後還有其它基督教會(循理會、拿撒勒人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陸續進入。以長老教會在排灣族的宣教而言,通過國外宣教師、平地教會傳教者、以及排灣族信徒的合作,許多排灣族人接受了基督的福音。〔9〕不過,不少排灣族人成為基督徒以後,卻遭遇新的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習俗之間的衝突。特別是受到外國與漢人傳教師的信仰教導,許多族人必須要在基督信仰與傳統文化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以今日角度來看,當時基督教宣教師與平地牧者普遍受到較保守的神學思潮所影響,多以負面或誤解的眼光看待排灣族的傳統宗教文化。他們認為原住民的宗教是「迷信」,許多文化傳統是「惡習」。典型的例子如下:
「關於迷信,可說多到無法說盡,如小鳥蛇的迷信,吃小米、吃飯的迷信,撒種收穫之迷信,死人之迷信等等太多了,這些迷信阻止了他們生活的進步,並使他們毫無自由。」〔10〕
在這裡與蛇有關的一切被視為迷信惡習的一部份,與基督宗教信仰不相容。依據這樣的信仰理解,教會面對排灣族蛇圖騰的態度,是相當負面的(參考本文2.2及3.1進一步討論)。這種拒絕的態度也影響生活的其它層面,包括宗教信仰、文學故事、藝術表達、教育,以及文化等各個方面。過去基督教會面對排灣族蛇圖騰時,較採取負面與拒絕的態度,其背後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探討:
2.1 福音與文化的議題
從台灣基督宗教宣教歷史來看,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西方宣教師大多來自較保守的信仰背景。在福音與文化的議題上,許多宣教師認為基督福音與亞洲文化是對立而且互不相容的。特別是不少宣教師(有意無意地)挾恃其西方文化的優越感,面對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落後社會」,更是輕視本地的文化。因此本地人要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時,就必須與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刀兩斷。早期排灣族的信徒深受宣教師與平地牧師這些觀念的影響,自然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也採取拒絕與排斥的作法。若從H. 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一書福音與文化對應的幾個不同模式來看,正是典型代表「基督敵對/超越文化」的模式。〔11〕
不過,時代在變遷,1980年代之後,新一代具文化自覺的原住民基督徒,開始反省影響上一代牧長與信徒的神學思潮,並且提出批評,甚至進一步呼籲要發展出本色化的神學觀。借用孔漢思(Hans Küng 1989)的觀點,就是採取一個「外來宗教本土化」(kontextuelle Inkulturation)的方式,〔12〕將基督信仰在原住民文化實況中表達出來。這種融合本土文化的趨勢在台灣天主教裡開始得比較早。由於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1962-1965,簡稱梵二)後續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後,在台灣的天主教會對各地的本土文化採取比較包容與開放的態度,例如1972年天主教會首度在新春彌撒之後,接著舉行祭祖禮儀,開啟一個福音與文化相容的新紀元。1980 年之後,在台灣不少地區的天主教會也將傳統文化節期轉化為禮儀的一部份,特別是在原住民部落的天主教會裡,這趨勢更為明顯。此外,近幾年來在基督新教裡,也有越來越多的神學工作者強調,基督信仰應當在台灣的文化中實況化或本土化(例如台灣本土神學的觀點)。不過多數基督新教的平地教會與原住民教會的牧長及信徒,害怕違背信仰的上帝,對自己過去的傳統文化仍然採取存疑的態度。在排灣族教會裡,不少人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對蛇的圖騰的態度仍有相當的保留。
2.2 對經文不同的解釋與傳承(Reception)
原住民教會對蛇的質疑態度,有很大的原因來自過去信仰的教導與聖經的解釋。特別是教會傳統裡,許多基督徒受到某些聖經傳統的影響,把蛇視為撒旦魔鬼的化身(參考創世記3;以賽亞書27:1f;啟示錄12:9, 14-15;20:1-3),卻忽略蛇也包含其它的象徵意義。
在蛇象徵負面意義的經文裡,包括創3伊甸園裡的蛇,這蛇被視為上帝創造中最「狡猾」的造物(3:1),甚至在舊約晚期以後成為撒旦的化身。〔13〕此外還有:
「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並殺海中的大魚。」(賽27:1)
這一節經文具有啟示文學的色彩,與古代近東的神話傳統有密切的關連,當中所指的三種造物:鱷魚(liwyätän)、蛇(näHäš)、及大魚(Tannîn),都是指宇宙中混沌的毀滅性力量,而上主制服了這些混沌的勢力,代表上主掌握這創造世界的次序。「蛇」在這裡顯然象徵毀壞的負面意義。〔14〕而蛇後來和戾龍、甚至魔鬼、撒旦的形象連結在一起,流傳在啟示文學的傳統中,延續到新約的時代。正如啟示錄所記載的: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啟 20:1-3)
在啟20:1-3這經文裡,蛇、魔鬼、撒旦成了同義字。〔15〕其實,在聖經裡面,蛇不盡然完全是負面的,也有經文以正面角度描述蛇的特性。例如,在耶穌的話語中,他一方面勸誡人們「要靈巧(有智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 10:16),另一方面他也指責惡人為「毒蛇的種類」(太12:34;23:33)。這些話正顯示,蛇是亦正亦邪的造物,具有正面與負面的多重意義。〔16〕至於到底蛇象徵正面或負面的意義, 那就要看它放在什麼樣的前後文/脈絡(context)裡面而定。
聖經裡正面描述蛇的意義,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民數記 21:8-9 的「銅蛇」。民數記 21:4-9 敘述,以色列人
「從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心中甚是煩躁,就怨讟上帝和摩西說:『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裏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於是上主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百姓到摩西那裏,說:『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上主,叫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上主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 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民 21:4-9)
這段經文清楚指出,那些被毒蛇咬了而中毒的以色列人,當他們抬頭仰望銅蛇之時,就會得到醫治。因此,銅蛇是醫治拯救的象徵。〔17〕而銅蛇這個圖像後來也幾次出現在新約裡,〔18〕特別是在約翰福音 3:14-15 如此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這段經文顯示,柱子上的銅蛇預表了十字架上的耶穌。約翰福音敘述的脈絡相當清楚指出,正如古代那些被毒蛇咬到的以色列人,當他們抬頭仰望柱子上的銅蛇,就可以化解蛇毒而得到醫治;同樣的,當人類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穌時,會得到永生。可見銅蛇與基督的關連極為密切,兩者都被掛在柱子上,銅蛇帶來醫治,而人子帶來拯救(永生)。
銅蛇的主題在早期教會中也扮演重要的意義。第二世紀末特土良(Quintus Tertullian 西元 160-225 年)在論拜偶像(De Idololatreia 西元 198年)一文極力反對製造雕像,因為它破壞了第二誡不可造偶像的誡命(出埃及記 20:4;申命記5:8)。不過特土良認為,摩西設立銅蛇卻是個例外,因為從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11的主張及約翰福音3:14的經文來看,銅蛇不是偶像,而是十字架的預表。它拯救人脫離魔鬼的使者——蛇的掌控。〔19〕在第五世紀(大約西元 430 年)羅馬城Aventin的S. Sabina教堂,裝飾著一系列二十八片用賽浦路斯香柏木雕刻而成的舊新約故事。其中一扇門的木刻圖像以銅蛇為前景,而背景陪襯著過紅海與穿越曠野的舊約主題(參考圖二)。〔20〕這浮雕突顯,銅蛇代表醫治與拯救,具有正面的意義。

以上的例子說明,銅蛇主題在早期基督教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這主題一直與耶穌基督的拯救有密切的關連。這樣的瞭解開啟我們不同的視野,一方面幫助我們修正過去負面的觀念,另一方面讓我們對聖經中蛇的象徵有較平衡的看法。
2.3 對宗教象徵與圖像的不同態度
M. Eliade 認為宗教的圖像、象徵符號與神話將信仰中非常深邃而隱晦的意義顯明出來。〔21〕基督宗教傳入歐洲,將各民族傳統的宗教圖像「重新添加活力、重新整合、重新賦予新的名字和信仰內涵」,〔22〕因此讓基督教信仰能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東正教對「聖像」(Icon)的態度正好說明宗教圖像表達出人類生命與永恆的上帝之間深刻互動的關係。東方教父巴西萊斯(Basilius)認為尊敬有形的聖像就是對無形上帝的敬拜,這觀念得到多數東正教會的支持,後來聖像尊崇成為東正教千年的傳統。〔23〕宗教圖像在西方羅馬天主教會也有悠久的傳統。特別是教堂裡面彩色玻璃繪製的聖經故事,以及各種宗教人物壁畫,對當時多數目不識丁的教友會眾,是培育信仰的優良教材。〔24〕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情況有了新的變化。主張改革教會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 拒絕中世紀教會許多的觀念,強調破除過去的傳統,重建人與上帝之間更直接的關係。〔25〕於是許多宗教的圖像在宗教改革者破除偶像的大纛之下,遭受池魚之殃。基督新教信徒強調人與上帝直接的關係,不需要藉助聖徒或其它東西做為中間媒介。不過他們在拒絕聖人崇拜時,所採取激烈的損毀舉動,卻也洩露心底嚴重的「焦慮與恐懼」。Karen Armstrong在「神的歷史」(1996)一書中對新教徒搗毀偶像的舉動,做以下的評述:
「許多新教徒與清教徒非常認真的看待《舊約》中詛咒偶像的教訓,他們把聖像與童貞瑪麗亞的雕像打破,而且把白漿投擲到教堂的壁畫上。他們瘋狂的熱情顯示,他們對冒犯這個易怒而嫉妒的神,仍舊和他們祈求聖徒代為求情時一樣的害怕。這同時也顯示,這種只崇拜神的熱情不是從冷靜的信念產生,而是從造成古代以色列人拆毀以希拉(Asherah)女神的竿子,以及他們鄰族罵不絕口的焦慮否定中產生的。」〔26〕
當代神學家宋泉盛在「第三眼神學」一書裡也提到:宗教改革時期,許多基督新教人士的搗毀聖像的作為,造成不良的後果,以及深遠而負面的影響:
[他們]「極端厭惡宗教圖像,於是大舉破除偶像。可是一旦掃除了所有的宗教圖像與象徵符號,它們所代表的究極實在,也很容易地從人民的宗教意識中消失。這種現象在抗議宗的教會,特別是歸正教教會的崇拜中,特別嚴重。崇拜變得空空洞洞的,『攝人魂魄、又令人興奮不已』的宗教經驗已經喪失了」。〔27〕
宋泉盛這一段話值得讓人深思,基督新教(改革宗)極力排斥宗教圖像與象徵符號的後果,不只切斷了教會傳統悠久的視覺藝術傳統,同時也對自身的信仰傳統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3、實際案例探討福音與文化的關係
近年來由於宣教神學觀的改變,各地興起本土神學的反省,促使新一代的神職人員、教會領袖與信徒改變了過去的一些想法。不過先前認為「福音與文化」相互衝突的保守觀念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一般信徒的生活。因此對福音與文化的議題,有必要做更深入的反省,並且在禮拜儀式與信徒生活當中實踐出新的信仰風格。以下我以兩個教堂的建築設計為例,來說明福音與文化相容並存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機會。
3.1 三地門長老教會的百步蛇圖騰爭議
首先以屏東三地門長老教會(排灣族)的教堂設計為例。這教會於1993 年初完工獻堂,它是一座排灣族傳統本色化的禮拜堂,設計者是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先生。為了教堂的外觀與內部設計,撒古流與教會建堂委員會曾經多次討論教堂的草圖設計。雙方在討論過程中,引發福音與文化相互詮釋的衝突,特別是百步蛇圖騰可否運用在教堂建築中引起極大的爭議。撒古流認為,傳統排灣族文化與百步蛇的關係非常密切,舉凡食、衣、住、行、娛樂,無一不與蛇有關係。〔28〕因此在他最先提出的教堂設計草圖中,將兩條百步蛇的圖騰融入在教堂的地板上(參考圖三)。他表達自己以下的看法:

「原本最早的構圖是從大門的兩邊以兩條百步蛇紋到前頭百步蛇頭相碰頭,然後,耶穌在這裡。這個圖案在排灣族裡面很多,而且我們的解釋是『賦予能力』的解釋」(指耶穌握著兩個蛇頭的角色)。〔29〕
不過,教會建堂委員會對此設計覺得不妥,並且質疑為何把「蛇」這代表邪靈的象徵,與耶穌放在一起?〔30〕因為他們認為,根據創世記 3:1-9 記載:蛇是屬於撒旦,是邪惡的。面對如此福音與文化的衝擊,教會建堂委員會顧慮到教會內信心軟弱信徒的緣故,所以拒絕讓蛇圖騰這「山地魔」出現在教會的空間裡,以免混亂人心。〔31〕建堂委員會因此否決了撒古流原來的設計草圖,請他另外繪製一個符合教會傳統的設計圖(參考圖四)。

雖然如此,撒古流個人卻有不同看法,他從基督信仰的觀點對蛇圖騰做以下的解釋:在創世記裡
「蛇受上帝的懲罰,用肚子行走;而在洪水之際,牠必定已得蒙上帝的赦免,方得進入方舟,上帝並沒有對他做第二次的審判;教會是接納罪惡之地,透過基督讓罪惡得到赦免,為什麼教會不能夠接納文化中的百步蛇;另,摩西的故事,銅蛇的拯救,信仰如何解釋。」〔32〕
然而,為顧及維護教會內的和諧氣氛,在教堂設計以及後來的施工上,撒古流都依照建堂委員會的決定來進行。其次,在教堂信徒兩邊座椅的中間走道上,鑲嵌著彩色的聖經故事圖案。其中有一幅在伊甸園內,亞當、夏娃與蛇互動的場景。在這圖畫組合裡,這條黑白相間的伊甸園之蛇,修長的蛇身上有腳。根據設計者的說法,這也是為了避免引起會友的疑慮,認為傳統的文化象徵放在教堂裡相當不妥,而採取的妥協作法。此外,原先有人提議,以橫豎兩條交叉的百步蛇圖騰來呈現教會講台上的十字架。不過,這也因為上述的顧忌而遭到否決,最後教會講台上也仍然懸掛著傳統的木製十字架。〔33〕
從三地門教會教堂重建的過程中,所引發的疑慮、討論與最後決議可以得知,蛇的圖騰確實在排灣族基督教會的牧長與信徒心中,造成不小的困擾,甚至引發福音與文化如何交融的爭論。教會基於牧靈的考量(信徒的接受度)因而否決了一項會引起爭議的新嘗試。不過卻讓福音與文化之間,仍然存在某種緊張對立的關係,需要做更深的對話與交融。
3.2 土坂天主堂的十字架與祭壇
相較於三地門長老教會的百步蛇圖騰爭議,台東達仁鄉土坂天主堂(排灣族)的設計顯得幸運許多。這天主堂內部的設計是個範例,用來說明傳統宗教文化如何融入基督信仰當中。教堂門面與祭壇都裝飾著排灣族百步蛇的圖騰,還有一些傳統象徵性的物件與主題也出現在教堂空間裡。
首先,教堂內十字架上耶穌的雕像結合了排灣族頭目/勇士與宗教傳統的造型(參考圖五):壯碩的身軀、身著傳統服飾、手臂上綁著彩帶、頭戴山豬牙編成的太陽花頭飾、頂上插著老鷹的羽毛。由於一般勇士頭頂插著兩三支老鷹的羽毛已經算是英勇了,而耶穌頭飾上卻插著七支鷹羽。因此如此耶穌的形象不只是排灣族傳統的勇士造型而已,他甚至比所有地上的勇士更偉大。而且在基督宗教裡,數字「七」還象徵完全與完滿的數字,因此七支鷹羽也富有強烈的宗教意義。此外,耶穌雕像的雙手、雙腳都有釘痕,肋旁也有明顯槍矛的刺痕,五個傷口流出鮮紅的血。這「五傷」的痕跡正是耶穌受難的記號,在天主教會的傳統裡相當為人熟悉。同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耶穌腳下的雙頭百步蛇。雙頭蛇的圖騰在排灣族裡對平常人是禁忌,卻是頭目祖靈像特有的記號。〔34〕雙頭蛇圖騰出現在十字架上耶穌的雕像上,強調耶穌崇高的地位與靈力。〔35〕從以上說明可以看出,土坂天主堂十字架上的耶穌造型,很巧妙地融合了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與排灣族傳統宗教文化的精華。

其次,教堂內祭台的雕刻再次展現排灣族的傳統宗教與文化的圖形。這祭台的四邊雕刻著十二使徒的頭像,每一邊出現三個使徒,其造型風格受到十架耶穌聖像的啟發,每個使徒頭飾上都有雙頭蛇的造型(參考圖六),〔36〕讓人一眼就認出它所具有的排灣族風格特色。這又是結合基督宗教信仰與排灣族傳統文化的一個例子。此外,祭台左右兩側,聖母瑪麗亞塑像下的供物器具,以及聖體龕,也流露排灣族的風格。

整體而言,土坂天主堂聖壇與十架耶穌雕像的設計,充分地反映出基督宗教信仰與排灣傳統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色。在基督信仰本色化的議題上,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範例。
4. 從牧靈的角度再思福音與文化的議題
從上面幾點的討論可以發現,基督教會過去對蛇的圖騰較採取消極排斥的態度。雖然這情形在最近幾年有些轉變,不過蛇圖騰與基督信仰的關係,以及福音與文化的議題在今日仍然急需做更深刻的反省與探討。從實際牧會/牧靈的角度來看,個人建議今後教會牧者與信徒可以加強以下的工作:
4.1 以重新解讀聖經來塑造新的信仰文化觀
前文提及三地門教會建堂時,遭遇蛇圖騰是否可以放在教會空間的爭議(參考本文 3.1),這衝突的原因大部分出在信仰觀(參考本文 2.1)以及聖經的解釋上(參考本文 2.2)。假如我們能考慮到福音本色化的策略,以及更全面整體地瞭解聖經如何描述蛇的意象,應該會對這主題有比較平衡的認識。也就是說,蛇不是只有一種負面的意義——撒旦魔鬼的化身而已。我們在聖經裡也同樣可以發現,蛇具有正面意義的例子。深入探討正面描述蛇主題的經文,尤其是民數記 21:6-9,會開啟我們另一個開闊而充滿希望的視野。代表醫治的銅蛇,與十字架上的人子(約3:14-15)密切地連結在一起。〔37〕如此的關連以及聖經解釋,對於排灣族蛇圖騰與基督信仰的融合,肯定會有正面的意義以及深遠的影響。我們需要更加努力用心,從聖經裡面找尋啟發的靈感以及聖靈的指引。
4.2 以融合美好的文化傳統來深化基督信仰
對蛇的尊崇代表排灣族悠久的文化,認識這文化傳統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聖經,並且形塑新的信仰觀念。排灣族的蛇圖騰以及族人對蛇的尊敬,讓基督徒以一個新的眼光來讀聖經,從讀經當中找尋新的啟發與靈感。對聖經新的瞭解有助於牧長與信徒對信仰有更深的瞭解,以及對這信仰的委身。
我們可以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認識文化可以深化基督信仰的意義。泰雅族與賽德克族裡自古流傳著「編織的上帝」觀念。〔38〕這編織的信仰觀表達,宇宙萬物的形成是透過 Utux 的編織而來,藉著這編織天地間出現人類、飛禽、走獸、魚類、山川與溪流、花草與樹木。他們的生命、命運與未來,都被緊緊地編織在一起,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對基督信仰與神學而言,從「編織」的角度來認識上帝的創造與生命的起源,這是非常有啟發性的信仰觀/上帝觀。這觀點啟發我們以一個新的角度來解釋聖經,以及認識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詩篇 139:13-16 描述詩人對上帝創造的奧妙,從心底發出讚美。特別是詩人對自己過去未出生之前,在母胎中已經受到上帝暗中的保護與照顧,發出感謝與讚美。
13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14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15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16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其中,第15節的「我⋯⋯被聯絡」(ruqqamTî,pual 字根rqm)這動詞的原文希伯來文rqm 正是「編織」的意思,它指向編織或刺繡而成的璀璨色彩與圖形。〔39〕而「地的深處」則反應出古代近東「大地之母」的悠久傳統。因此,15 節可以重新做如下的翻譯:「我在暗中受造,就是在『大地之母』的深處被編織」。這意思是說,詩人告白著,上帝編織著人的生命,讓生命在大地之母的孕育下默默地成形。這詩句反映出古代的生態神學的觀念,對我們瞭解現代的生態神學有相當的幫助。現代生態神學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是主宰者與被主宰的階級關係。而是彼此相互依賴、共存的「網絡」關係。在上帝的編織之下,人類與天地萬物形成一幅多彩的「網絡」圖案,彼此相互支持與互助。這是一幅美麗的生態「網絡」與「編織」。如此看來,我們可以從聖經經文與原住民泰雅爾族/賽德克族「編織的 Utux」概念的相互交融中,更深刻發現編織上帝的動人信仰觀念。這樣的發現,無疑更加豐富了我們對自己與生態的瞭解與珍惜,同時也更加深我們對上帝的信仰與愛。
4.3 更新的信仰與傳統的文化彼此相互提昇
從前面幾個例子讓我們進一步認識,解釋聖經、瞭解福音、與珍惜文化可以形成一個正面的互動與循環,各方相互激盪與交融的結果,讓我們的信仰更加深刻, 對自己原住民的文化更深的欣賞與愛惜。在福音與文化的一來一往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讓福音與文化彼此不斷的對話,相互深化瞭解、而且彼此相互提昇。這種交互循環的互動模式對我們從事神學的教育與反省有很大的幫助,特別在原住民保存自己的文化傳統,以及委身於宣揚基督的福音,都有深遠的助益。
結語
最後,我以尼波山頂銅蛇紀念碑的圖片作為結語(參考圖七),盼望藉此能喚起更多人關心福音與文化的互動與相互成全。〔40〕在這圖片裡,出現尼波山上豎立一座金屬雕塑「銅蛇」。尼波山位於約但河東岸,在死海東北角的一座山。而這座銅雕是出自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藝術家Giovanni Fantoni 的作品,今天它仍然屹立在尼泊山頂。而銅雕的背景是死海及約旦河彼岸朦朧的應許之地—也就是現今的以色列地。申命記 34:1-7 記載著:年老的摩西爬上了尼波山頂,上帝讓他從這山頂看見以色列人民將要進入的應許之地。眼前的這片土地是上帝向他們的祖先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以色列的子子孫孫將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並且世世代代紀念上帝偉大的作為與恩典。雖然摩西無法親自進入應許之地,但是上帝卻讓他在這山頂上,眺望應許之地的全景,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全境一覽無遺。摩西遠眺著那個無緣進入的應許之地,雖然深感遺憾卻也得到安慰。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看一下這座「銅蛇」雕塑的造型,會注意到一方面那條銅蛇纏繞在赤紅的銅柱上,這是民數記 21:4-9 豎立銅蛇情節的再現。這座銅雕紀念在曠野中上帝藉摩西豎立銅蛇,拯救以色列脫離死亡的陰影。另一方面從雕塑的頂部來看,蛇頭環繞的角度以及銅柱向兩端的伸展,讓人聯想起約翰福音 3:14-15 的描述:正如摩西當時舉起銅蛇,今日人子也要被舉起,所有仰望他的人要得到永生。在 Fantoni 的雕塑裡,蛇的頭與人子的頭很巧妙地融合為一。我覺得這座雕塑對民數記 21:4-9 與約翰福音 3:14-15 兩段經文做了一個非常巧妙地的整合詮釋,生動而震撼人心。我相信 Fantoni 的雕塑所突顯的意義,對我們探討「福音與文化」的主題有很大的啟發。想像一下排灣族的原住民,站在祖先的發源地— 大武山(Kavulungan/Tjagaraus)上,〔41〕遠眺著屏東與台東地區起伏的山巒,前瞻未來子子孫孫的前途…。如何將自己從耶穌基督所領受的福音以及祖先傳承下來的傳統(蛇圖騰、節期、文化)做一個巧妙的融合,讓世世代代的子孫得到祝福。這是值得原住民基督徒委身投入,一生努力的目標。
最後以一位深具文化自覺的排灣族教會長老的一段感言來結束本篇報告:
「排灣族的『神』(Tsemas)和『上帝』是一樣的,上帝創造世界上的各種文化, 因此,各種文化都是好的,…沒有理由要求排灣族人用以色列人的方法來敬拜上帝,反倒是應該用排灣族的方式(文化)來敬拜上帝。…排灣族人(或土坂人) 應該努力發揚排灣族文化,排灣族的文化如能發揚光大,不正意味他們更能敬拜上帝嗎?」〔42〕
本文原刊於《玉神學報》 第13期(2006年6月)
*本篇論文首次發表在2002/03/16天主教台北利式學社主辦的研討會中。此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台灣原住民族傳統信仰與基督宗教的相遇:本土實踐經驗工作坊暨研討會」。我以「蛇的圖騰在天主教與基督教會中的運用:排灣族蛇圖騰與基督宗教的詮釋——傳統文化的宗教表現問題」為題發表論文。經過內容的修改與補充之後,在此發表,願上帝祝福玉山神學院六十週年慶。
註釋
〔1〕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文化與福音對話的著作出版不少,例如參考蔡彥仁等著,《原住民文化與福音的對話》,(台北:台灣世界展望會,2004)一書中的數篇論文與反省。
〔2〕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18-21。
〔3〕以下幾則故事參閱尹建中,《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輯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人類學系,1994),頁183-185;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頁20。
〔4〕參考甦濘・希瓦,〈由東方教會的反圖像爭論:談有形象徵在排灣中會三地門教會中的使用問題〉學期報告(台北:台灣神學院,1999/07/09)的舉例。
〔5〕關於土坂部落的起源,參考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100ff;有關土坂部落的現況,參考傅君,《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頁136-141。
〔6〕有關排灣族人與蛇的其它故事,參考尹建中,《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輯研究》,頁218-220。
〔7〕參考吳銅燦,〈西部排灣(含魯該)族傳道簡史〉,《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鄭連明主編(台南:台灣教會公報,1965),頁427。
〔8〕參考酋卡爾,〈排灣族教會宣教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永望,1998),頁191。
〔9〕各地排灣族部落對基督宗教的接受程度有些差別,不過整體而言是歡迎多於拒絕。有關排灣族的宣教史,參吳銅燦,〈西部排灣(含魯該)族傳道簡史〉,《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425-434。1960年代參與排灣族宣教的平地傳教者有許有才、黃素娥、吳銅燦、高俊明等人。
〔10〕吳銅燦,〈西部排灣(含魯該)族傳道簡史〉,《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426。描述排灣族的「宗教與迷信」、「惡習」以及「善俗」,特別反映出該文作者作為一個「圈外人」(outsider)的觀點:宗教方面,他提到「該土民拜三種神」,即創造人之神(tagaraus/撒拉班)、海神(varaluval/哇拉陸哇勒)、祖先神。而所謂的「惡習」則包括:頭目專橫、殺人、淫亂、菸酒、不求進步,「⋯⋯其它惡習尚多,不能一一枚舉」。至於「善俗」作者列舉:互助、有無相通、不自私、善待客人。
〔11〕H. 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賴英哲、龔書森合譯(台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86)。列舉五種模式:「基督敵對文化」、「基督屬於文化」、「基督超越文化」、「基督與文化處弔詭關係」以及「基督轉化文化」。John H. Yoder, “How H. Richard Niebuhr Reasoned: A Critique of Christ and Culture,” in G. H. Stassen, D. M. Yeager and John H. Yoder, Authentic Transformation: A New Vision of Christ and Culture (Nashville: Abingdon 1996), pp. 31-89. 對這五種模式提出反省與批評,他提到,Niebuhr 後來曾進一步澄清,上述五種福音與文化的模式都有它的優缺點,而且可能同時並存。因此Niebuhr 認為,對以上的觀念使用母題(motif)的字眼應該會比用模式(type)更恰當。相關討論參考 Yoder, “How H. Richard Niebuhr Reasoned: A Critique of Christ and Culture,” p. 45.
〔12〕孔漢思分析過去四百多年來西方基督宗教(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傳教師面對亞洲宗教文化不同的對待模式。他列舉了七個不同模式(1.「外表的同化」,2.「信仰的混合」,3.「不同層次的互補」,4.「傳教士間的衝突」,5.「文化帝國主義」,6.「反傳教」,7.「外來宗教的本土化」),並一一提出反省與評價。孔漢思本人支持最後一種模式「外來宗教本土化」,並強調它的重要性。孔漢思所說的這一個模式,其德文原文是“kontextuelle Inkulturation”,更正確的翻譯應為「處境的本土化」。這觀念與基督新教神學家黃彰輝所提倡的「實況化神學」(contextualization)有相似之處。詳見秦家懿、孔漢思合著,吳華譯,《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台北:聯經,1989),頁227-269。
〔13〕參考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1-11: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Trans. by John J. Scull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pp. 237-239.
〔14〕參考Otto Kaiser, Isaiah 13-39: A Commentary (Trans. by R. A. Wils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4, 德文原版為1973年出版), pp. 221-223.
〔15〕有關蛇、魔鬼、撒旦三者的連結,參考Jürgen Roloff,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Trans. by J. E. Alsup.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德文原版為1984出版), pp. 148-149; pp. 226-227.
〔16〕參考K. R. Joines, “The Serpent in Gen 3,”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vol. 87, no. 1 (1975): 1-11.
〔17〕參考Jacob Milgrom,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Numbers (Philadelphia/New York: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0), pp. 173-175; Walter Riggans, Numbers, The Daily Study Bible Series, Old Testament (Phile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pp. 157-160.
〔18〕根據林前10:1-11,使徒保羅用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的例子,作為哥林多教會信徒生活的警戒,尤其10:9以蛇咬做為負面提醒的教材。
〔19〕有關特土良的論證,參考Günther Stemberger, ed., Jahre Christentum: Illustrierte Kirchengeschichte in Farbe (Erlangen: Karl Müller, 1994), S. 138-139. 從銅蛇與毒蛇的區別,我們再次看見蛇的正負面意義。
〔20〕圖片取自Günther Stemberger, ed., Jahre Christentum: Illustrierte Kirchengeschichte in Farbe, S. 139.
〔21〕參考Mircea Eliade,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Trans. by. P. Mairet.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2), 12ff.
〔22〕參考宋泉盛著,莊雅棠譯,《第三眼神學》,(台南:信福,1993修訂版),頁250。引述Mircea Eliade,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pp. 174-175.
〔23〕有關東正教西元七至九世紀的圖像論爭,以及從反對圖像到尊敬圖像的過程,參考Günther Stemberger, ed., Jahre Christentum: Illustrierte Kirchengeschichte in Farbe, S. 267-270.
〔24〕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中古世紀流傳的「窮人的聖經」(Biblia Pauperum),首先在1460-1490 年間以木板畫版本出現,書中的圖片對當時一般不識字的信徒發揮很大的宗教教育功能,參考Albert C. Labriola and John W. Smetlz, The Bible of the Poor [Biblia Pauperum](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Paul Tilich對基督新教的反圖像傳統做了很深入的反省,參考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119ff.
〔26〕引自Karen Armstrong著,蔡昌雄譯,《神的歷史》,(台北:立緒,1996,英文原版為1993年出版),頁465。Asherah 在中文聖經譯名為「亞舍拉」,亞舍拉為迦南宗教女神,是至高神伊勒的配偶。而譯文的「竿子」應是指「木柱」,為亞舍拉女神的象徵物。
〔27〕引自宋泉盛,《第三眼神學》,頁244。
〔28〕參考甦濘・希瓦 1999/07/09 列舉的實例。
〔29〕參考甦濘・希瓦(1999/07)引述撒古流的口述。
〔30〕參考甦濘・希瓦 1999/07。
〔31〕參考甦濘・希瓦 1999/09。
〔32〕引自甦濘・希瓦1999/09。
〔33〕者從排灣族神學家童春發口述得知。
〔34〕瑞士籍天主教神父艾格里博士(Dr. Hans Egli)為筆者解說時提到,這尊耶穌雕像於 1980 年代中期完成後,掛在天主教堂啟用。當時出現在這雕像上面的雙頭蛇圖形,曾經引起土坂部落頭目家族的不滿與抗議。因為他們認為,雙頭蛇圖形只有頭目/巫師家族才可以擁有,其他一般人不能僭用。比較土坂部落包頭目家族祖靈屋裡的祖靈木雕像上面的雙頭蛇造型,以及天主教堂耶穌雕像上的雙頭蛇圖形,可以發現兩者間確實有不少的相似性。還有一個有趣的後記:1980年代,土坂天主堂的十架耶穌受苦的雕像,委託屏東古樓社的某個排灣族藝術家來製做。原先教會交付的雕像設計圖,是耶穌站在一個船錨上(船錨在西方天主教會裡,與耶穌的拯救有密切的關連)。不過,這船錨的造型對排灣族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東西,以致那位受委託的古樓社藝術家「誤將」船錨的設計圖形,雕刻成雙頭蛇的造型,後者對排灣族人是熟悉的圖案。當土坂天主教會代表去驗收雕像成品時,原來對這個雙頭蛇的完成品有些遲疑;不過,最後教會代表還是接納這件作品,於是這雕像被運回土坂天主堂,懸掛在教堂內的祭台牆壁。
〔35〕在排灣族的人觀中,一個人的靈力(legum)是祖靈眷顧與個人靈魂結合的表現。靈力的強弱影響個人、家族與整個部落的興衰禍福。靈力、祖靈與家屋是排灣族文化中三個最重要的核心觀念,參考傅君,《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頁20-21。
〔36〕祭台是土坂本地的藝術家Sapari的創作。根據艾格里神父與Sapari告訴筆者,Sapari受到教堂十架耶穌雕像的啟發,接受教會的委託,完成教堂的祭台。後來,在2001年,Sapari 也受邀請參與土坂村包頭目祖靈屋的設計,以及參與雕刻各樣的器具。甚至包頭目祖靈木雕像的修復工程,也由Sapari 親手完成。從這裡可以感受到,在土坂部落裡,本族藝術家、傳統藝術與教堂藝術三者之間有密切的關連。
〔37〕參考Albert C. Labriola and John W. Smetlz, The Bible of the Poor [Biblia Pauperum], pp. 3-4以類型學(typology)的角度來說明銅蛇(type)與人子(antitype)兩者的關係。
〔38〕有關賽德克族「編織的神靈」,參考 Siyac Nabu(高德明)口述,Walis Ukan(張秋雄)譯註,〈非人的境遇——賽德克族看霧社事件〉,收錄在 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主編《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台北:前衛,2001),頁19-69,45f,52f,53f。泰雅族的「編織的上帝」,參考高萬金,〈編織的上帝:詮釋泰雅爾族傳統信仰的經驗〉,收錄在陳南州主編,《台灣神學教育協會年刊》,第一期,(台南:教會公報,2000),99ff。
〔39〕參考查爾士・包宜著,王茂彩譯,《孩子不同、需要不同》,(台北:學園,2001),頁12-13。此外,從rqm 同一動詞字根引申的名詞「編織的人」(röqëm),則出現在(出26:36;27:16; 28:39;35:35;36:37;38:18, 23;39:29)。這都是指用彩色絲線,或是金線、銀線編織的師傅。
〔40〕圖片取自Inge Bruland, Ins gelobte Land: Auf den Spuren von Mose (Stuttgart: Deu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1), S. 172。
〔41〕Kavulungan意為大拇指、眾山之母、真正的老山;而Tjagaraus 具宗教意義,除稱呼大武山以外,泛指天;參考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頁295。
〔42〕引自傅君,《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頁140。
參考書目(按照年代排序)
英文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Eliade, Mircea.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Trans. by. P. Mairet.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2.
Kaiser, Otto. Isaiah 13-39: A Commentary. Trans. by R. A. Wils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4.(德文原版1973)
K. R. Joines, “The Serpent in Gen 3,”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vol. 87, no. 1 (1975): 1-11.
Walter Riggans, Numbers, The Daily Study Bible Series, Old Testament. Phile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Labriola, Albert C., and John W. Smetlz. The Bible of the Poor [Biblia Pauperum].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cob, Milgrom.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Numbers. Philadelphia/New York: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0.
Roloff, Jürgen.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Trans. by J. E. Alsup,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德文原版 1984)
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1-11: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Trans. by John J. Scull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Yoder, John H. “How H. Richard Niebuhr Reasoned: A Critique of Christ and Culture,” in G. H. Stassen, D. M. Yeager and John H. Yoder, Authentic Transformation: A New Vision of Christ and Culture. Nashville: Abingdon 1996.
德文
Stemberger, Günther. ed., Jahre Christentum: Illustrierte Kirchengeschichte in Farbe. Erlangen: Karl Müller, 1994.
Bruland, Inge. Ins gelobte Land: Auf den Spuren von Mose. Stuttgart: Deu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1.
華文
吳銅燦,〈西部排灣(含魯該)族傳道簡史〉,收錄在鄭連明主編,《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1965。
H. Richard Niebuhr著,賴英哲、龔書森合譯,《基督與文化》,台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86。
秦家懿、孔漢思合著,吳華譯,《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台北:聯經,1989。
Karen Armstrong著,蔡昌雄譯,《神的歷史》,台北:立緒,1996(英文原版 1993)。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第三眼神學》(修訂版),台南:信福,1993。
尹建中,《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輯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人類學系,1994。
酋卡爾,〈排灣族教會宣教史〉,收錄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永望,1998。
甦濘・希瓦,〈由東方教會的反圖像爭論:談有形象徵在排灣中會三地門教會中的使用問題〉學期報告,台北:台灣神學院,1999。
高萬金,〈編織的上帝:詮釋泰雅爾族傳統信仰的經驗〉,收錄在陳南州主編,《台灣神學教育協會年刊》,第一期,台南:教會公報,2000。
Siyac Nabu(高德明)口述,Walis Ukan(張秋雄)譯註,〈非人的境遇——賽德克族看霧社事件〉,收錄在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主編,《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台北:前衛,2001。
查爾士・包宜,王茂彩譯,《孩子不同、需要不同》,台北:學園,2001。
傅君,《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
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蔡彥仁等著,《原住民文化與福音的對話》,台北:台灣世界展望會,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