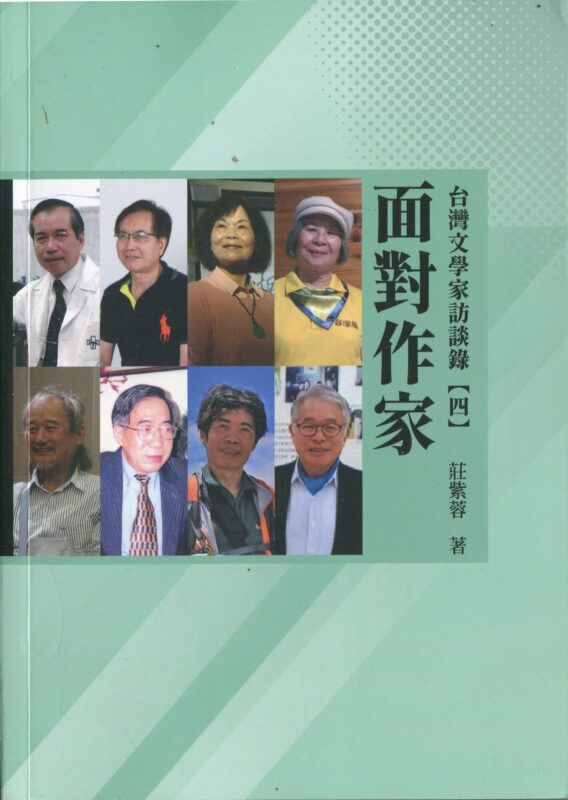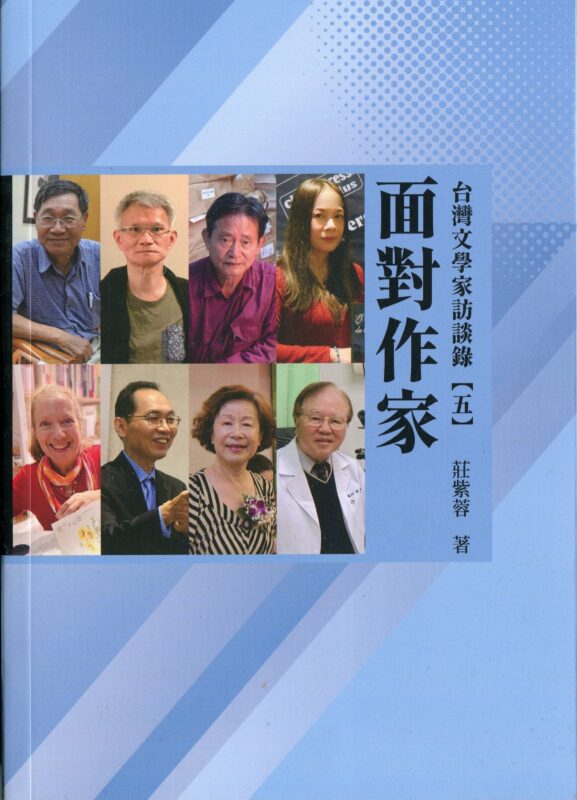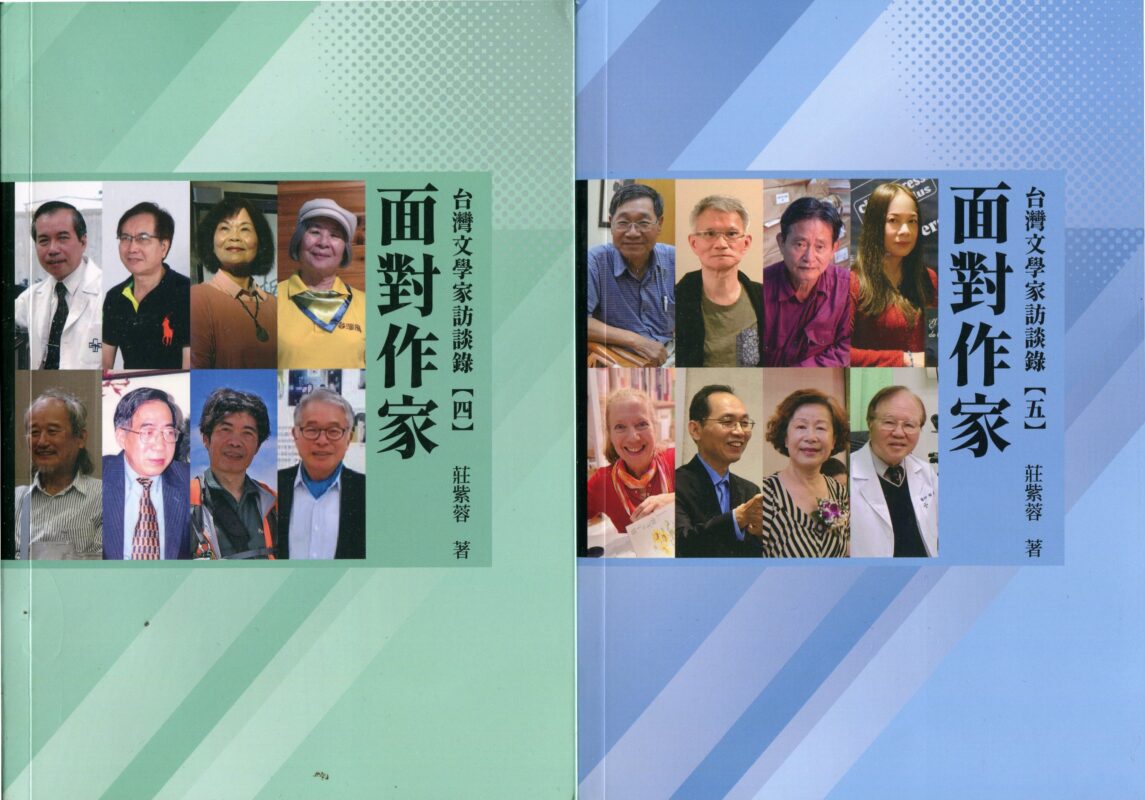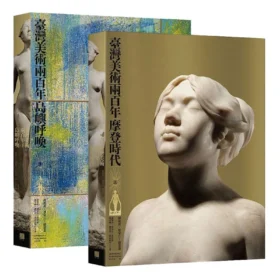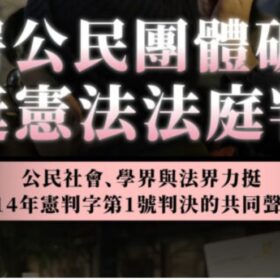《面對作家:台灣文學家訪談錄》第四、五冊〈序文〉
周婉窈
(這篇序文寫的時候曾貴海醫師過世不久,等收到這套書後不久李魁賢先生也離世,令人難過。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文學哪一天才能成為台灣人精神生活不可割離的一部分?作者謹記 2025/2/10)
莊紫蓉老師曾自1997年起訪問24位台灣文學作家,於2007年集結出版三冊《面對作家:台灣文學家訪談錄》(一、二、三),這是台灣文學的重要著作,不管是入門或深入研究,都是必讀之書。(詳細內容請見張俐璇教授序文)其中有幾篇訪談錄,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張教授提到的〈葉石濤: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我格外喜歡〈曾貴海:孤鳥,樹人與海〉,相當深入完整。今年6月29日莊老師在高雄見到曾貴海醫師,曾醫師表示很喜歡那篇訪談錄,歡迎莊老師再來訪問。這個2006年之後的續篇,精采可期,但是非常令人痛心惋惜的是,曾醫師於8月6日凌晨離開我們。
這次出版的《面對作家:台灣文學家訪談錄》(四、五)是莊老師從2017年開始進行的訪談,中間經過三年疫情,預定2024年秋冬出版。在這一年出版應不是刻意安排的,不過,2024對於台灣、台灣文學卻有特殊的意義。
距今一甲子之前的1964年,是戰後台灣歷史的關鍵年份。為什麼這樣說呢?這一年4月文學家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6月《笠》詩刊問世,9月台大彭明敏教授和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擬散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破被捕。後者是政治事件,師生付出極大的代價。前二者屬於文化範疇,《台灣文藝》於2003年結束,《笠》詩刊則延續至今,今年5月至12月於全台四個地方舉辦60周年特展,並有多場講座。我的學術訓練不是文學,無意在這裡寫我不懂的台灣文學史,只是想就我對戰後台灣歷史的了解來分享一些看法。
《台灣文藝》、《笠》,以及「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都在1964年出現,當然不是彼此約好(哪裡可能?!),但之所以「不約而同」就很值得深思。簡單來講,這是從1945年戰後台灣再度受到殖民統治──更加嚴厲的殖民統治──台灣人經過長時期的受壓制,失語/緘默/沉潛之後,在第20年終於開始「做些什麼」。如果有一種樹叫做主體或主體性,那麽,在這一年我們看到它正從島嶼的土地中努力冒出來(發芽/發穎puh-gê/ huat-ínn)……。戰後KMT/ROC黨國統治下的台灣,政治犯忌非常危險,不是等著被送到綠島,就是馬場町。文學或許比較不顯得對殖民政權有立即的危險,它像水一樣,涓涓滴滴,要穿石談何容易,但日久自成溪河。
《面對作家》前三冊約有三分之二的作家出生、成長於日本統治時期,他們不只歷經兩個殖民統治,語言上也面臨非常巨大的改變。也因此以台灣為主體並彰顯其主體性,可以說是他們必須思索、必須面對的巨大課題。語言的轉換是他們最大的噩夢。相對而言,後續的這兩冊《面對作家》的受訪者雖有生於日本時代者,最早是1943年,終戰時才二歲,尚無記憶,因此可以說是成長於戰後台灣、接受完整黨國教育的世代。他們和文學前輩最大的不同在於:一、沒經歷時代的大巨變。二、沒經歷書寫語言的大改換。
這兩冊書共有16位受訪者,如同第一冊有一位非台灣人馬漢茂(德國人,台灣文學研究者),第五冊也有一位法國人伊麗莎白,她用中文寫詩。另外,第五冊也有一位非作家巫宜蕙,她是巫永福的女兒。這兩位不論的話,這兩冊的14位作家,就出生年可以這樣歸類(按年齡與章次排序):
1940年代五位:喬林(1943)、賴欣(1943)、鄭烱明(1948)、林豐明(1948)、莊金國(1948)
1950年代八位:利玉芳(1952)、陳坤崙(1952)、謝碧修(1953)、李昌憲(1954)、蔡榮勇(1955)、陳明克(1956)、林盛彬(1957)、葉宣哲(1959)
1960年代一位:陳秀珍(1960)
因此,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共五位;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共八位,如果只差一年的1960出生者也併入計算的話,就是九位。
這兩個年齡層的作家有何不同?以下只是整理個大概,因為莊老師並不是拿同樣的題目去問所有的受訪者,無法做有效統計;受訪者沒談到不表示不存在這樣的經驗。
首先,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們,可以說是第一個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世代,但因為「去古未遠」,大都親身聽聞過二二八(喬林、鄭烱明;僅舉例,或有遺漏,下同),有強烈的外省人vs.台灣人的感受(賴欣、林豐明、莊金國),接觸到早期的反國民黨人士(莊金國),他們也敏銳感受到戰後初期的語言現象(喬林、鄭烱明)。他們和日本時代出生成長的作家如陳千武、葉石濤有比較密切的接觸(賴欣、鄭烱明),可能因此還能感受他們的苦,比如鄭烱明就說他們的「語言轉換是很痛苦的」(第四冊,頁46)。換言之,他們雖然生於1945年前後,還是接得上日本時代的人物和「遺緒」的世代。
如果我們能將前三冊的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許達然、吳晟、曾貴海、李敏勇、莫渝、江自得,一併探討的話,相信會看出更多具有時代意義、更具揭示性的現象,不過,那已經超出本序文的範圍,也不是我能在短期內整理出來的。
前三冊的受訪者並無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這應該是第四、第五冊的特色。他們就讀國民學校(請注意:是國校,不是國小,1968年九年義務教育實施有國民中學/國中,才有國民小學/國小)時,已經是1956至1966之間,黨國的殖民統治・支配日趨穩固,黨國教育的效力更加強大。不要忘記,1950年代是白色恐怖最血腥的年代,黨國的控制越來越嚴密。在這十年間上學的台灣孩童接受的教育可以說相當一致,他們的經驗也反映了這個一致性。
他們沒有經歷時代轉變的大風大浪,也因「吾生也晚」,沒機會接觸到戰後過渡期的舊時代「遺緒」,他們的訪談大都環繞在學校教育,見證惡性補習(葉宣哲)、體罰(葉宣哲、林盛彬),以及取締台語掛狗牌(陳明克)等。對男作家而言,當兵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驗,有人見證了軍隊中的殘暴(蔡榮勇)、抓耙仔(陳明克)、被作票(李昌憲)。外省人/主流vs.台灣人/本土的問題依舊存在(陳明克、李昌憲、賴欣),也有人因為同學而認識反國民黨異議人士(陳坤崙),我們也看得到黨外運動與美麗島事件的影響(林盛彬、葉宣哲)。客家文化和原住民的身影也看得到(利玉芳、陳坤崙);也有詩風由外省主流轉向本土者(謝碧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紀最小的陳秀珍,在工廠工作,同時讀夜校,幾乎沒有休息,過著「非常黑暗的生活」、「感覺沒希望的生活」!
以上只是取其普遍性,至於他們之間的城鄉、階層的不同,只能略去。他們和我是同個世代,讀來特別有感。我成長的年代,台灣人已經完全被噤聲,沒有人會和你提二二八,更不要說正在發生的白色恐怖。所以這個世代的人沒聽過二二八、白恐是很通常的事情,但巫宜蕙例外,父親是文學家巫永福,她的二伯在二二八期間被抓,受到正常人無法承受的虐待,回來後精神出問題;她的六姑丈白恐時期被抓,在新店關了10年……。(第五冊,頁241)這篇訪談錄有很多重要訊息,連結到橫跨兩個時代的前輩們。最後想提的是,1950年代出生者接觸到的前輩最被提及的是李魁賢與陳千武,關係比較像前輩提攜後進,和1940年代出生者與前輩作家的接觸應該有所不同。
戰後的台灣,尤其白色恐怖時期(1949-1992)就主體、主體性的主張與彰顯而言,一直是民間走在體制/政府的前面。而民間又以台灣文學界走在最前面──但現在卻未必如此,反而有高度自我體制化的情況。
《笠》詩社能延續一甲子,在世界上可能很少見,或許可算是個奇蹟。60年來參與者至少有三個不同的世代,這其間的變化(延續與斷裂)要如何分析,留待將來台灣文學史研究者。我是行外人,在這裡只想提出一個我看到的三代間的延續。
在第二冊的訪談錄,陳千武說:「我剛剛談到我在台中一中時,為什麼會反對改姓名運動,這都是因為從文學而認清了自己:我自己有我的自我,為何要改姓名?」(頁287)那時候陳千武還是現在高中生的年紀,不能不說思想很早熟。
台灣就是台灣,為何不能就叫做台灣?在第五冊,陳秀珍說:「……人在國外,『台灣』就會變得很敏感,一旦國家的名字被講錯,心裡就會過不去!」、「如果我個人的名字被說錯比較無所謂,如果是國家被誤稱就完全無法忍受。」(頁132)但問題在於:如同海關官員問陳秀珍:「你們明明是台灣護照,為什麼上面要印中國字樣?」(頁133)這是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不要留給下一代。
關於自稱台灣,可能很多人還有這樣的敏感度,但不知道曾貴海「在台灣走不出中國」的痛感,有沒有被台灣文學界的新生代繼承?他在《憂國》(前衛,2006)提到,他要從高雄的家到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我住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後面,開車要經過廣東街──中正文化中心──中正路,然後上中山高速公路。在文化的地景與權力地圖上,有個巨大的文化中心叫作『中正文化中心』,它象徵著中心文化的權力。而我就在那條連結人與人及車道上仍然虛構著統治者已失去的土地街路上行進,接著我必須要走上中正路才能接中山高速公路。如果不行駛這些以統治者名字命名的道路,絕對沒有辦法走到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頁201-201)我不知道18年後,這個路線有沒有「改善」,至少到現在在台北精華區很難走出中國。中華民國的立法院就是被中山南路、青島東路、鎮江街、濟南路包圍住,真的就是道地的中華民國立法院,不是台灣的立法院,所以才需要「青鳥行動」吧?──走不出中國,只好用飛的?
台灣文學的詩人作家們早就認知/認定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殖民統治,曾貴海直接講「殖民統治」(《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前衛,2006),李敏勇用比較客氣的「再殖民或類殖民」(《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雙重構造的精神史》,九歌,2019),但在台灣學界的「自我建制化」之下,這樣清楚的界定,現在很難看到。明年,KMT/ROC佔領支配台灣就滿80年了,比起日本殖民統治的50年已經是1.6倍了,但濟濟前輩努力澆灌的主體、主體性的樹,有長大到足以取代外來的中華民國嗎?顯然沒有。
建立台灣的主體、彰顯其主體性,細節不能不注意;不管上帝或魔鬼,都藏在細節裡。我們真的必須從「小事」做起,最近一個多月我的三位師長相繼過世,讓我心情很低落。他們都是台灣建國主義者,但當我收到家屬寄來的訃聞時,加倍難過──因為訃聞都用「民國」紀元,不用西元;還有明明生在日本時代,也用民國幾年!這是小事嗎?我認為不是,我們應該更加用心,才能告慰一生追求獨立建國卻無法看到的故人。
最後,在此我要向莊紫蓉老師致上最高敬意。27年來有莊老師勤勤懇懇為我們訪問本土派詩人、作家,實在是台灣的幸運。謝謝莊老師!
(寫於202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