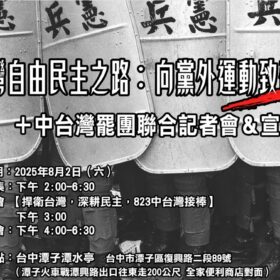復興鄉參訪活動心得:石門.奎輝篇
林易澄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我們一行人在周婉窈老師與中村平老師的帶領下,展開了為期四天的復興鄉參訪活動。復興鄉的居民以原住民泰雅族為主,是中村平老師撰寫論文時的田野地點。泰雅族的羅馬字拼寫,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寫作「Atayal」,本文根據泰雅族民族議會的用法,作「Tayal」。因為我個人的身體因素,沒有走完全程,只參觀了石門與奎輝,未能進一步看看後山爺亨部落的情況,覺得相當可惜。不過短短一天的行程,也留下一些感觸——或許不能說是很有條理的感想。這一天裡,聽Masa Tohui(黃榮泉)先生回顧他個人戰後的經歷,介紹了石門水庫遷移事件;也看到了黃榮泉先生父親Tohui Hola(日本名:原藤太郎)與姊姊原照子的墓地;在晚餐後的訪談裡,又聽他談到近年的原住民族運動。儘管只是短短一天,把這些線索聯繫起來,卻像是勾勒了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百年來的Tayal歷史。

黃先生的解說從南島民族開始,談到這個島嶼上的各族群,介紹泰雅族的傳統文化。然後到了近代,一批批新的族群來到了這裡:移墾的漢人、日本殖民政府、國民黨政權,隨著臺灣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Tayal在與外界的互動中,逐步被納入近代政權治理的邊陲。在這過程中,作為歷史行動者的Tayal,也逐漸變得無聲,特別是從石門水庫遷移事件來看,隨著「文明」日益迫近,Tayal已經不像早年還能與日本軍警打上幾場戰役;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一再被當局草率的遷移政策撥弄其命運。

在這背景下,直到一九八○年代以後,包括Tayal在內的臺灣各原住民族,才慢慢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爭取自己的權利。二○○五年在Tayal民族議會的大會手冊中,大會發表了以下的〈Tayal民族土地宣言〉:[1]
一、Tayal民族在其領土早已建有自治實體與從未承認外來政權之事實。……至晚近不及400年,有荷蘭、明鄭、清廷等國相繼攻略臺灣,其間時有舉兵企圖侵犯吾Tayal民族之領土,但均遭吾Tayal民族之抵抗,因而未能得逞。
二、日、清兩國因甲午戰役,締結講和條約,均認為吾Tayal民族為其化外之民而非其人民,其領土亦認為屬於吾Tayal民族所有。日本據台後即企圖侵佔吾等領土,而為此巧立理論抹殺吾Tayal民族人權,以得逞掠奪領土之目的,卻引發轟動一世之征蕃(指原住民族)戰役。經20餘年(1895~1923年)戰役,終以溝(媾)和息事。日本人遂將吾Tayal民族領土劃為「蕃地」,……等全域土地(悉依Tayal民族傳統領域)認定為吾Tayal民族之領域,其面積大凡六十餘萬公頃。
三、經【舊金山合約】生效後,凡被日本政府侵奪之原有領土,應即時歸還與原主(Tayal民族)之正當性與主張。……
四、政府對Tayal之領土侵奪及殖民侵略之事實。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在其戰後時局動盪不安之際,政府卻未經求證吾Tayal民族領土之歸屬,擅訂『台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限制吾原住民之土地使用。之前於一九四九年發佈全國戒嚴令限制人民自由、對原住民則以捏造事端,加以白色恐怖壓制,使吾Tayal民族不得伸張主權。
在這些線索構成的敘事裡,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的近代國家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過程:在「文明」進步的目標之下,地方相異的、自主的文化體系,如何被國家納入一致的、中心的治理秩序之中。不論是外來的殖民治理,抑或是國家內部的現代化過程——在某個意義上,臺灣原住民族的課題,兩者都涉及了。不過,這樣的歷史敘事,仍然留下了有待補充的疑問。
黃先生的父親Tohui Hola,是第一位接受日本教育擔任巡查的Tayal族人。昭和十五年(1940)當殖民政府打算丈量部落土地收歸管用時,他切腹自殺,留下遺言,希望日本人「要以誠對待原住民、不要欺騙、彼此信任」。處於兩個文化之間的Tohui Hola,在死時,對於Tayal族的未來,有著什麼樣的想法?在日本帶來的「文明」與自己族人原有的文化之間,他曾經想像過什麼樣的可能性呢?
我也想起Tohui Hola 的兒時玩伴,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擔任故鄉公醫的Losin Watan(日本名:日野三郎,漢名:林瑞昌,這次活動第二天的行程便是拜訪其子林茂成先生)。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他在另一個政權之下被判處了死刑,遭到槍決。此一涉及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的政治案件,即〈宣言〉裡提到的「捏造事端,加以白色恐怖壓制」。就目前公開的檔案與相關訪談所知,當時被捕的角板山Tayal族與阿里山鄒族精英,雖不能斷定參與了省工委的計畫,但確實有過一定的往來與配合,將族人的未來置於國共內戰的局勢下考量;同時在部落年輕的一輩中,也有更加積極,並思考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參與者。

在面對外來國家的過程中,當地的人們是如何主動地去應對新的局勢呢?他們只是單純的、無聲的、原子般缺乏組織的被動者嗎?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樣的被動者是怎麼在歷史的過程中形成的?如果並不只是這樣,那麼他們與各時期的外來政權之間,有過什麼樣的抵抗與合作?——特別是在軍事的勝利之後,近代政府所要的不僅是綏靖邊陲,而是有效且深入的治理,它同樣需要地方的合作。在這個「之後」中,形成了什麼樣的新地方秩序;在其中,如果曾有過不和諧的聲音,那是什麼樣的形式?又如何影響到一九八○年代以後的變化?
由於拜訪的時間有限,當時並沒有進一步發問。晚上回到民宿休息時,在與中村平老師的談話中,又從另一個方向得到啟發。我的疑問是,一直到今天,原住民族關於民族議會的想法似乎也並不一致,這是為什麼呢?是否是在威權體制下被分化的影響?(問答大意如此,記憶細節可能不盡完全)中村老師則反問我,在外來者到來之前,原本的原住民是不是能用一個「統一團結」的概念去想像呢?他們的分類,更多時候接近「這個流域的族群、下面的流域的族群」這樣的區別。(Tayal以部落為基本單位,基於共祭、共獵、共負罪責等社會功能,形成若干地緣兼血緣關係的組織,部落之間屬於平等地位,不相干涉內政。)從這個角度來看,儘管在特殊的事態下,Tayal族各部落之間有時會形成暫時的攻守同盟(pinhaban),彼此間也有相近的文化與經濟、社會往來,但是以民族(nation)這樣的近代概念來理解,則有失其情。這裡並不是說,〈宣言〉中「Tayal民族在其領土早已建有自治實體」只是「被發明的傳統」;相反地,應當去問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Tayal族人在與外來者接觸的經驗中,將「民族」的概念納入了自己的思想詞彙中,並且以之來思考現存自治實體的定位,從而去追溯,在這過程中,部族的菁英頭人以至於一般民眾,如何在與外來者的新體制的相遇中,尋找部族與自己的位置。
同時,這個過程,顯然在不同部族內部、不同的傳統政治文化間,會有不同的發展。另一方面,在這過程中,部族內部並非鐵板一塊的情況,是否也影響了日後新體制走向的可能性?例如,在鄒族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湯守仁等人的政治案件中,除了他們與省工委人員接觸的原因外,也有一說指出,當時部族中分為兩派:一為高、湯等受過日本教育者,一則為守舊者所組成,而後者藉機採取與國民黨政權合作的方式來打擊高、湯等人。

這樣的想法,並不是要去否定「Tayal民族」的概念,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歷史的過程:它(Tayal民族)並不是作為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在與外界的歷史互動中形成的。近三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界中後殖民、後結構的轉向,使得民族、文化的本真性,變成一個有些曖昧的議題。[[2]研究者一方面試圖為過去在現代化過程中被壓抑的少數族群文化發聲;一方面又察覺到,許多文化的特質與分類也形成於這一歷史過程中。例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經由人類學的研究,將臺灣各地的原住民予以分類,辨識出「Tayal」的存在;而到了近年原住民族正名運動中,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又希望將自己從Tayal族中分出。這提示了我們族群界定的歷史性,以及這一歷史性與當前現實之間的複雜關係。在這裡,歷史建構論並不意味著虛無主義,因為重點並不在於「民族」究竟是本真性的存在,還是近代的產物;更重要的當是去考察這一歷史過程為何,其中產生了什麼樣的權力關係,這一關係通過與原有文化的互動,又如何影響該族群的自我意識,進而部族的人們如何參與這一歷史過程,然後形成了今日「民族」的樣貌。
記得中村老師提到,當他開始進行研究的時候,有人覺得他的研究對象已經不是那麼純粹的原住民文化了。但是他卻認為,不純粹的、與外界互動的地方,豈不是更值得研究嗎,這才是他所要的人類學(大意如此)。也曾聽過人類學系的同學提及,近年來作原住民研究題目的人變少了。因為現在的部落與外界已經牽連太深,不可能像日本時代的學者鳥居龍藏、森丑之助那樣,去描繪出一個部族文化的靜態全景;也不像一九七○年代的學者還能目睹劇烈的變化如何改變部落的社會。當他整理部落的宇宙觀時,往往覺得這與田野地的實際生活距離很遠。從今天這「不純粹」的狀態向前回溯,我們的研究對象,當不再只是文明開化之下的被動者,也不再是靜態的、與外界無涉的人們,而是參與了歷史變遷的行動者,這一面向仍有待進一步的梳理。學術的課題往往跟著時代的處境而變,或許,這樣的問題,正要求著新的解答方式吧。以歷史的角度去考察近現代以來,部族中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們,如何想像作為一個「實體」一分子的自己,帶著這一想像,或顯或隱地,參與地方秩序以至於國家體制建構的過程。這樣的嘗試,或許能讓我們對「Tayal民族」的認識,以及未來的可能性,有更多的擴展。同時,也能讓作為外來者的「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為何,有更深的體察。
[1] Biru Bkgan na Tegpusal Mintxal Melahuy nqu Ginlhoyan Pspung Zyuwan Tayal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手冊(2005.6011 Sinkina Tayal Kyokay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五尖教會),頁11-12。
[2] 一個有名的例子是,1989年人類學家Allan Hanson發表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一文,指出紐西蘭毛利族許多被視為文化傳統的儀式活動,乃是伴隨英國政府在殖民過程的參與所形成,引起當時正致力於復興族群文化、爭取政治自主的毛利族人學者極大的不滿。可參考Allan Hanson,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1, No. 4 (1989), pp. 890-902.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01/11 網站文章)